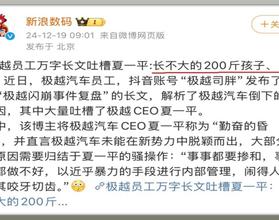近日有澳洲朋友问我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议,此前我也与其他朋友聊过该话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涵盖儒、道、释、兵、墨、法等各家思想;经、史、诗、赋、词、小说、音乐、书法、绘画;以及礼仪、服饰、饮食等,有精神,有文艺,有器物。学多少,学哪些,取决于孩子或大人兴趣在哪方面,或愿意下多大功夫。限于能力与篇幅,不能全涉及,在此整理部分建议,供诸君参考。

现在很多古代经典书籍都能买到,西方国家有些学校也教。如果有兴趣,不应只求学到一点表面,因为有许多深层的问题值得学生和老师思考。再者是看待历史人物、事件、书籍、文章的角度和观点,这比读书本身重要太多。现代许多人读古书的视角和思维都出了问题,譬如将马克思主义定于一尊,硬套中国文化,或以进化论看历史,还过度以自然科学视角分析,钻到事件、数字的牛角尖里,却轻视或不理解古人思想,或以理论框架框死。中国大陆受中共和马克思主义洗脑严重,香港、台湾、国外好一些,但也有尚待改进之处。
学中国传统文化,受近现代与西方理论影响过大不一定是好事,这毕竟不像经济学、自然科学。打个比方,弹古筝、拉二胡总不能以钢琴、小提琴为指导。以史学为例,清朝道光、咸丰以前都很好,道咸以后走下坡路;西方史学近三百年才像样,而中国古代史学著作三千年间璀璨夺目,延绵不绝。外国专门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著作未必优质,譬如日本史学家稻叶岩吉于1914年写成《清朝全史》,民国史学家萧一山少年时读过此书,批评其疏漏错误颇多。
清末民初虽大量引进洋学,大师林立,其观点却未必正确。譬如今人采用自梁启超以来之见解,以为中国传统政治一概为君主专制,但若你仔细研究,不难发现此说法不准确。另外,马克思主义信徒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定义中国古代,更是荒唐。中国古人绝大多数都是自由公民,没有奴隶社会。封建一词古已有之,在中国古代指天子分封诸侯,《左传》称“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意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之说。自秦朝起,中国不再适宜被称为封建。钱穆是对此问题认识较清晰的史学家之一,此外,梁漱溟也反对以马克思主义史观看中国历史,这两位均是民国学术界的大人物。民国初年以来,中国一些激进分子缺少对传统的敬意,要打倒孔家店,反理学,将外来文化皆捧上神坛,其破坏程度虽不及后来中共邪党发起的文革,却也扮演先锋角色。那时与激进潮流对抗的有钱穆、梅光迪、吴宓等人,坚持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建议各位谨慎对待民初以来的著作和人物,有些虽不是共产党,但其过度批判传统的观点亦不足取,不宜默认1949年前的著作都能放心阅读。比如鲁迅徒有虚名,不仅品德不好,文章也不如被吹捧的那样厉害,且对传统猛烈批判,过犹不及。中共很喜欢他,他曾骂谁,谁在大陆就被批斗。

我推荐钱穆于1939年撰成的《国史大纲》,这可谓是每位华人应读的史学巨著,其观点中正,内容严谨,深入浅出,黄仁宇评价他为“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钱穆后因反共南下香港,对中共邪恶本质与中国传统文化之珍贵认识颇深,他另著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史学名著》等,都值得一看。另外,我建议大家了解一下以梅光迪、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这两位学者均留学于哈佛大学,民国初期担任教授,与新文化运动唱反调。学衡派相对保守,捍卫文言文与儒家精神,可惜在中共篡国后遭到打压。但学衡派的价值和影响非凡,他们是活跃于香港、台湾的新儒家的源头。
以上我简单讲述了近一百多年来学术文化圈良莠不齐的状况以及对传统与历史的歪曲。各位切莫以为专家知名度高就一定可信,现代迄今才短短一百年,以后评价怎样尚不可知,很多经过千百年时间考验的大师都在古代。下面我主要讲书籍方面,谈一谈学传统文化读原典原文的重要性和博学通学的重要性,以及怎样学。

重原著 博且通
中国古书自《隋书·经籍志》开始正式分类为经、史、子、集四大部。以下参考清代《四库全书》逐一简介。
经主要指儒家推崇的经典,含《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乐经》、《孝经》、《论语》、《孟子》以及小学等。
史指不同体裁的历史著作,包括正史、政书、编年、传记、纪事本末、史钞、史评、载记、别史、杂史、目录、职官、诏令奏议、地理。
子指诸子百家,如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医家、农家、释家、小说家等,还包含天文演算法、术数、艺术、谱录、类书。
至于集,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文集,包括楚辞、诗文评、词曲、别集、总集。比如《文选》、《诗品》、《文心雕龙》、《东坡词》等均归类于集。

古人治学一向重视通,现在人说文史哲不分家,也是这道理。读中国古代史时需学经,先有思想上的共情,否则难以理解古人的行为,因为两千年来经书都可作为做事前的参考。现代人忽视经学,再去读古代史,一定会有损失。就连古人,若经学功夫不够,也会导致自己的著作有缺。
唐代刘知几写过一本《史通》,史学价值高,却不够理想,熟稔经学的人读后会发现作者不擅长经学。果然,刘知几小时候不喜欢读《尚书》,而特别喜欢《左传》。据《新唐书》记载,“年十二,父藏器为授《古文尚书》,业不进,父怒,楚督之。及闻为诸兄讲《春秋左氏》,冒往听,退辄辨析所疑,叹曰:‘书如是,儿何怠!’父奇其意,许授《左氏》。逾年,遂通览群史。”刘知几擅长史学,可惜因学问有偏,终究在写作时暴露了短板。
经学对文学而言同样重要,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讲文学评论,称各种文体都起源于经书:“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刘勰学识卓越,能看到本源与大处。学问做得越广越好,尽量阅读四书五经、文学、史学的原典原文,比泛泛地听别人转述好许多,若只听老师讲个大概,则不能算得上真正学会。或许会觉得文言文有点难,但不必担心,许多都有注释,一步一步来。

读原文可以品味出许多背后的思想和精神,尤其是史书中微言大义的文字。譬如读《春秋》,孔子为何写“郑伯克段于鄢”?这段历史事件讲郑庄公与弟弟共叔段之间的战争,用白话说,即郑伯在鄢这个地方打败了共叔段。试想,为什么不称“庄公”,而称“郑伯”?为什么要用“克”字?为何不写作“克其弟于鄢”?
《左传》讲解得很清楚:“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共叔段为争夺权力而造反,不像弟弟该有的样子,所以不称他为弟。郑庄公与共叔段如两个国君交战,“克”是用于敌人的,郑庄公视弟弟为敌,所以说“克段”。郑庄公身为君主兼哥哥,当看到共叔段有反叛迹象时未及时阻止并引导他归正,这属于没尽到兄的责任,所以称“郑伯”,讽刺郑庄公失教。不写“出奔”,是因为郑庄公有杀弟弟的意图,这也是作者对庄公的谴责。“郑伯克段于鄢”短短六字隐含褒贬,而作者态度却不是直白表达的,所述的确是事实,而非议论和说教。
孔子作《春秋》时周道衰颓,他有归正道德的目的在其中。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上至天子,下至大夫,无论地位多高,都可以批评,而立场则藏于事与文中。《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史书最重要的部分是义,文字和文体是史书传递义的桥梁,各家记载的事件基本上一致,读书的功夫不应只下在字面和事件上。我们衡量作者,重点是透过其义看其史识,未必认同,但应分清主次。在史识之前,先要有史德。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讲道:“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有立场是很正常的,现在许多媒体也都有,好的媒体能尽力保持客观中立。面对某些人和事,如希特勒、纳粹集中营、中共迫害异见人士,若仍保持所谓“中立”,则是良知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中立?与其说摒除主观成分,不如说摒除私心。任何一个作者都不可能做到100%没有主观,只能最大程度抑制主观的干预。若要给受迫害者发声的机会,则属于站在公道的一边,无可厚非。

公道,用古人的话说,属于天。天、人本就合一,人心符合天的时候,天与人便是完美的一个整体。当产生违背公道的私心时,人的部分就妨碍了天。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历代治史与著史者追求的最高目标便是如此,其中“究天人之际”最耐人寻味。天与人的关系到什么程度最合适?又如何将天人之际客观展现给读者?在天道面前,人有其所能为,有其不能为,亦有其无能为力之处。章学诚《文史通义》谈史德,也讲天人之际,认为“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在写史书过程中,私尽量不妨碍天,这也是要求客观。客观不是一种空洞的标准,而是需要很谨慎、平和、公正且专业的文字表达,《文史通义》称:“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好文重在气和情,“气贵于平”,“情贵于正”,“夫气胜而情偏,犹曰动于天而参于人也”,气不能过激,思想和情绪不能不正。我们现在评价媒体文章,也可参考此见解,看其是否私的部分过多。

司马迁《史记》就是“究天人之际”的典范,他提出这一说,实际上自己也是致力这样做,尽量不以人碍天,保护历史的本来面目和纯度,既求真,更求道,班固《汉书》评价《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史学家若能同时具备很好的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相当不易,司马迁就是这样千年难遇的人,我们读《史记》,不该只钻进字眼里、事件里,更要看作者的史识。
在深入《史记》前,可以先了解此书好在哪里,他创立纪传体的意义,透过《报任少卿书》和《太史公自序》走近他的内心和生平;之后再细读他怎样写项羽、韩信、货殖列传,思考他为何在世家中将吴太伯放在第一位,在列传中将伯夷排在第一。他把项羽破例列入本纪,排在秦始皇、汉高祖之间,便是其史识卓越之处。灭秦之功,首推项羽,这是肯定了项羽影响历史演变的重要地位;但项羽也像秦朝的微缩版,骤兴骤亡,所以重点突出他的盛衰经过,和秦朝兴亡、西汉开国形成对比,以其为转折点记叙从秦到汉的脉络。吴太伯和伯夷的作为都是无为之为,虽无惊天动地之大事,然其精神影响后世千年——以让权为贤,以高节为美。吴太伯是兄,本有望继承王位,却淡泊权力,走到荆蛮之地,“文身断发,示不可用”,既是智慧也是美德。在吴太伯下方,司马迁还记叙了让位季札之事,这也是不争之美德。他的叙述很客观平和,同时隐约让读者感受到强调这些事的意义。纪传体的优点也在于此,可以保留大事件容易漏掉而对后人思想影响颇大的所谓小事,兼顾到无形之精神。倘若我们只看一个缩减的白话翻译版,只知道《史记》写了哪些重大事件,就容易漏掉许多关键的地方。

以上我简单举例讲了学古书时读原文的重要性;重点关注什么;经学、文学、史学是难以割裂的一个整体。按照《文心雕龙》观点,文学源于经学。在汉朝,史学尚未独立于经学之外,《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将史书归于春秋一类,唐代《隋书·经籍志》正式以经、史、子、集分类,可见学术的变化。我们做学问,应当知其大,探其源,从基础学起,从源头学起。
从源头学,包含按时间顺序自远到近学。如读历史,从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的神话开始了解,以及三皇五帝的故事,明代张居正为万历皇帝讲的历史课本《通鉴直解》便是从三皇五帝开始的。《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体裁为记言。其次是编年体,以时间为顺序编撰,以《春秋》为代表,通常需结合《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读。再往下到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之后《汉书》等正史均效《史记》体裁。从《尚书》起,一路下来到《汉书》,都是最重要的,不宜略过,而后面的正史可以挑著读,如果精力不够。到唐朝又有一大创新,即杜佑《通典》,是政书体的先河。记言体、编年体、纪传体、政书四大体例的代表作我们应当熟悉。再往后有宋代郑樵《通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与《通典》合称“三通”,也非常重要,读“三通”有助掌握古代政治制度。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可谓写得最成功的编年体通史,他和司马迁合称“两司马”,在史学界地位非凡。相信大家多少读过《资治通鉴》,建议同时参考张居正的《通鉴直解》,浅显易懂,很适合小孩看,毕竟张居正的讲稿针对的就是10岁的小皇帝。清初王夫之《读通鉴论》也可作为辅助。

学经、学文,通常先从四书五经开始,读经的同时,已经在潜移默化地提升文言文能力。读文学的朋友们应留意,假设你对唐诗宋词感兴趣,不宜只关注唐宋,最好先对时间靠前的作品有些了解,至少读过《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汉魏五言,以及萧统《文选》。应先了解风、雅、颂、赋、比、兴六义,以及诗兴、观、群、怨的作用,《论语·阳货》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是《诗经》和社会、政治紧密相关的意义。
读四书五经不应忽略《易经》。对于神话和《易经》,读者或许不全信,但这些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有些内容不能因为科学未能证实就跳过。中国古人一向重视人与天、神的关系,最早的教育与宗教信仰紧密相关。古代有一个重要官职叫作太常,主管祭祀和宗庙,兼管教育,这是信仰、政治、教育紧密相联的体现之一。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重要的大事就是祭祀和军事,祭祀属于常事,代表对神、天地和祖先的敬意。即使在现代,此话同样有启迪意义,一个国家想强大,不单要富国强兵,更需要坚守信仰。

此外,《道德经》、《齐物论》、《孙子兵法》、《高僧传》、《传灯录》等也建议看一看,懂得道家、兵家,以及将外来佛教汉化后的文化,还有其他百家。中国古代的思想绝非一成不变,自汉武帝后儒家影响虽大,但东汉后衰微,而老庄思想再兴,魏晋时流行玄学;隋唐时佛教达到鼎盛;宋明发展出新的儒家,理学大兴。可读的书太多,尽情自由选择,同时应注意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由博返约
有一个问题,想必中外皆有人思索过,即如何以简练的语言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精神。此问题确难回答,学者多在广博与细节处下功夫,但由博返约同样重要,得学会提炼和总结。钱穆曾以“道德精神”概括,即“自求其人一己内心之所安”,既不是在理论上探讨是非,更不是较量利害。钱穆所说内心所安或可理解为顺从自己的良心。
我试总结,中国传统文化,或许可概括为天人合一的修炼文化;中国传统思想和精神重视心中坚守之道不轻易为外界所动,视内在胜过外在。儒、佛、道三家均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回顾历史,佛家、道家通常要远离世俗修炼,最终要成神;儒家所言修身则是在世俗中,最终要以天下为己任,在做事的过程中也在修炼。儒、佛、道三家修炼都要向内修心,心正,向外表现自然也正。儒家的礼,其本质也是修心,外礼需有内德的支撑。《礼记》曰:“行修言道,礼之质也。”“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孝经》曰:“礼者,敬而已矣。”无论忠信、义理、敬,还是行为有修养、言谈符合道,都需向内在心性上修。《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先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再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内向外,自下而上,自小至大,一切基础在于个人的内心。

但中国古代有许多类人,不单儒、佛、道三家,更大范围看,思想有怎样鲜明的特点?《诗经》序中说:“发乎情,止乎礼义”,本是用于文学评论的话,却也非常适合概括中国古人的思想与言行。人类当然有好有坏,但人性本善,皆有爱亲人之心与恻隐之心,中国人的孝道其实是人性的体现之一。现代有人将忠、孝、仁、义、礼、信视为束缚,这是一种曲解,本来天与人为一体,人心即是天心,美好的品德为人自带。对他人仁爱,孝敬父母,是发乎情;看到小孩即将掉入井中,无论是谁家的孩子,是否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目击者都该产生怜悯之心,上前救人,如《孟子》所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也是发乎情。如果人心处在道德水准未下滑的状态,那么发乎情几乎等同于符合礼义。中国古人的精神有一特点,即在生命与道德之间抉择时,宁愿舍生取义,在利益面前亦然,这也是止乎礼义的体现。
以春秋时代的刺客鉏麑为例,他既非圣人,也非英雄,只是历史上处于特殊处境的一个普通人。晋灵公派鉏麑暗杀大臣赵盾,鉏麑抵达赵家后悄悄观察,发现赵盾很早就起床了,穿好官服后坐著假寐,等候上朝。鉏麑见赵盾如此尽职勤政,不忍心杀这样一位贤臣,但自己肩负任务,既已答应国君,若不杀赵盾,便是违背君命,不守信用。进退两难之际,鉏麑撞槐自尽。中国人说盗亦有道,鉏麑之事可谓刺亦有道,他的选择也是“发乎情,止乎礼义”。他非儒家、道家、佛家,亦谈不上高尚,却能坚守自己心中的原则,这种原则既非法律规定,亦非宗教要求。

无论夏商周还是秦汉以降,都可见自觉自律守义之人。春秋时卫国发生劫持孔悝的兵变,子路身为其下属,立即赶去救援。子羔劝子路没必要送死,子路却非常坚定,说食人俸禄,大难临头时不能逃避。此可谓在生命危险前保持超强的责任感。在打斗时,子路的帽缨被敌人斩断,他说,君子就算死,也不能让帽子丢掉。之后他弯下身捡起帽子重新绑上,同时被敌人杀死。子路本可以抛弃礼义,却在临死之际坚持不失礼。又譬如南宋文天祥、陆秀夫,明末夏完淳,可谓舍命坚守气节与民族大义。
以上自觉取义之举发生于动荡环境下,诠释了“虽千万人吾往矣”。也有一些处于日常生活中,不牵涉生死抉择。如男人皆有爱美女之心,这是发乎情,元代画家赵孟𫖯想纳妾,妻子管道升以《我侬词》委婉劝阻,赵孟𫖯被感动,打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可谓夫妻之恩义胜过纳妾之情欲。又如季札之自律与诚信,记载于正史中,传为佳话。有一次他与徐君见面,徐君很喜爱他的剑,但不好意思开口表示。季札当时看出徐君心意,因还有其他事要做,来不及将剑赠给徐君。待季札再回到徐国时,不幸徐君已经去世,他便将剑挂在徐君坟墓旁的树上。随从人员觉得不可思议,认为徐君已经死了,不必把剑送给他。季札回道:“我在心里已经许诺了。”在一般人看来,许诺往往都需说出,心里答应怎能算数?但季札就是如此自觉守信,不因外界变化而改变心中原则。
古代类似的事不胜枚举,可以为,可以不为,即使不这般做,也能找理由为自己辩护,但他们终究选择不随波逐流。人固有求利求生之心,亦有仁、义、礼、信、忠、孝存于心间,当不可兼得时,甘愿选择后者。唯有平日有意或无意间修身,才会做出如此选择。

早在儒家之前,中国人就已形成浸入骨子里的道德标准。后世的新思想,如孔孟、董仲舒、陆九渊、朱熹、王阳明的学说,无一不是建立在复古的基础上。
所有大儒皆向往以前的圣人。孔子敬仰周公,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然而圣人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人人均可经过修身达到,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孟子》说:“圣人与我同类者。”“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人性本善,圣人之心和普通人之心本是同一类心,在受污染前,可通于天。宋儒陆九渊说:“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明儒王阳明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圣人就在每个人自己心里,每个人都可以经过修身成为圣人。他又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在王阳明看来,天下没有心外的理,向内心摒除私欲就可以获得理,若内心纯净,表现出来自然就包含忠、孝、仁、信。从先秦至宋明,都可见儒家一脉相承的修炼内涵,修的方向即向内返回本性。
下期我将进一步展开讲更多书籍与心得。
本文由看新闻网原创、编译或首发,并保留版权。转载必须保持文本完整,声明文章出自看新闻网并包含原文标题及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