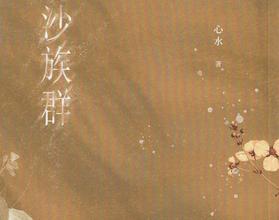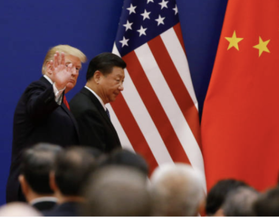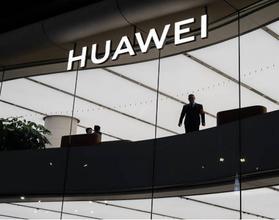中越两国的骂战越来越激烈,边界无时无刻在发生著零星的冲突:好奇的民众是不能满足于全面封锁下的新闻内容,单方的党报全是一面倒的报导,不真也不实。
元波已经养成了个危险的习惯、在每晚临睡前偷偷的用短波收听澳广或伦敦电台,从这两个电台的评论及时事报导里知道些消息。有时、会无意中收到强有力的北京广播,充满了战斗火药味的对越南辱骂。听到忘 形,往往是婉冰生气的把电源切断。
朋友相见,窃窃私语里绝大部份是在暗中交换著各自收听的新闻,世界消息就如此的在民众中靠这种方法传播,效力也极大。
有一晚,元波兴奋的呼叫婉冰“快来听,好消息 !”
她放下手上的毛线,快步走到床边,静静站了一会,才说:“还不是老消息,讲来讲去,都已讲了几个月啦!你不厌吗?”
“这次是行动了,三艘船已经在几十万群众放鞭炮欢送里启航了。”
“ 只派了三艘船?有多大,可以载多少人?三百艘还没法载完呢!”婉冰一连串的问号,很不以为然的语气,像冰水从头淋下,把发热的希望之光泼冷了。元波说:“当然不会一次撤完呵!有行动总比老是吹牛好,是不是?”
“我才不相信,共产党耍的全是花昭。”
“等著瞧、有好戏看就是了,你走不走?”元波接捺不下心中的高兴,喜形于色。
“看你那么高兴,别说我专泼冷水,如越共肯放人,十年还轮不到我们呢!几百万人的数目,只派出三艘船来,你也会当真?”婉冰深思熟虑的维持一贯的看法,
“可能先派几艘船做为试探性质,顺利的话再多派啊!总之,我们的祖国肯出力护侨,我们就不必再受气,不必再当海外孤儿,为什么不高兴呢?”
“事实很快证明,我也希望如你所言。”
“元波不再多说,自得其乐的整晚转著台,美国之音,伦敦,澳广、日本、北京,从各不同的消息来源证实那个令他雀跃的“撤侨”果真开始了。
第二天、市面沸沸腾腾,奔走相告,华埠堤岸的广大华族同胞,都喜气洋洋,大家都憧憬著回乡的美梦。故乡!对重视乡土观念的华侨毕竟是强有力的引诱,祖先的根源地,一旦可以回去,有谁愿意再流浪呢?
越共的大批警察,公安密探增强了在街上的巡查;报纸的头版新闻,刊登了党中央的文告。对中国的派船事件,当成挑衅式的侵略,声明如中国船只胆敢越雷池半步,公开进入越南头顿海外水域。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海军、空军将狠狠的把来犯的敌船击沉。
唯一的电视台上,许多节目临时取消,部分华人社团领袖被专访播出,分别用中、越语骂中共政权。
街坊会纷纷集合、所有华人都有了机会大骂自已的祖国,元波也被迫在会上对中国的“非法行动”严厉的指控,口里讲的和心中想的背道而驰。人人心里明白、口是心非、一级骗一级,越共要的都是这种玩意;谁说真话就倒霉,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谎话世界。他们用谎言取到政权,用谎话统治著国家,也必要用谎话使自己壮胆。所以、真话是不被接受的一种罪恶,除了在共产世界呆久了,才能明白,没有生活在共产主义‘天堂’里的人,怎么解释,也没法使他们相信那是存在的事实啊!
紧张的气氛一天天增加,好像一个气球,吹进去的气一天天多,球越来越大,已经涨到快破裂爆炸了。
中共三艘打走撤侨旗帜的船队,终于到达了越南南方距西贡百多公里的头顿市外,停泊在国际公海上。全南方华人都引颈以待,万方瞩目轰动世界、中国史无前例的撤侨行动将要开始了。
中国人终于扬眉吐气了,分布世上三千多万华侨、华裔从此不再是“海外孤儿。”睡狮已醒,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元波心头的喜悦兴奋,也像个快破裂的气球,越飘越高,越飞越远。
越共宣布在水域布了鱼雷,也派出了海军战舰。沿海巡视,准备对入侵的中国船只迎头痛击。
南中国海阴霾满天、战云密布,局势扣人心弦 。
侨胞们狂热兴奋已渐渐冷却,热度退下,三艘船日夜徘徊在国际水域上,不敢再越雷池半步。
雷声大、雨点小,十多天在中越双方不进不退的骂战声里,南越两百多万华人的情绪已被失望取代。膨胀的大气球没有炸破,气体泄掉,剑拔穹张;战云笼罩的海域,三艘撤侨的中国船队,鸣金收兵。满载三船南越海风归去,也载走了全球三千多万侨胞的希望和兴奋。载不走的是泪水和耻辱,是印支几百万炎黄子孙任人残踏的凄凉命运。
船只返航的消息播出后,许多华侨和元波一样的流泪伤心,气愤与平,海外孤儿的命运已注定了。倒是婉冰,平静如昔,仿佛她早已认命,没有寄予希望,也就无所谓失望。
元波归纳了整件事的前因后果,越想越怕,对自己天真的寄望感到幼稚可笑。
堤岸城的光𪸩已经暗淡了,人往人来,表面没什么变化,可是,总很敏感的在社区中看到垂头丧气的华人。元波注意著,以前兴高采烈满脸堆笑的五官已经难再在路上发现。大家都心事重重,对于自己做为一个海外华人,不但没有光彩,而且危机四伏,走投无路,随时任人凌辱杀戳(柬埔寨几十万华人死于非命的冤魂可以明证。)一个民族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还能笑呢?怎么还可以抬起头来呢?
时间在颓丧的气氛里移动,地球绝不会为了人世间的喜怒哀乐而放慢旋转。
一九七八年的农历春节在粉饰太平的鞭炮声中来临。市面多了许多流浪汉
,乞丐成群结队在国营饮食店外徘徊,等著抢客人留下的残羹馀菜。街头巷尾的各色赌档林立,公园的阻街女郎在太阳没下山、已迫不及待的展示乳波臀浪,沿街叫卖她们的肉体。
汽车的流通量已很少,“的士”也少见;人力三轮车 ,马车和脚踏车这些古老交通工具渐渐占用了道路。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西贡,随著名字的沉没已完全失去了姿彩,更因灯光管制(发电厂没有足够燃料发电。)整个城市五光十色、闪烁的灿烂市容已不再有了。黑暗!滋生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罪恶。无业的流浪汉、丐帮子弟们,和许多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所谓‘阶级敌人’,黑五类份子的家属们,为了生存,都被迫上梁山,在夜街里对往来的人下手,抢劫已经不是新闻了。
晚上、没要紧的事,元波已不敢独个儿乱逛。通常和老杨站在门前纳凉,交换些消息;多数的时间是教女儿认识些中文,此外是扭开收音机,偷偷听些澳广的播音。也喜欢点唱节目,新春时节的点唱特别多,那晚、竟没想到听见在美国的元浪点给他一首生日歌,他高兴到手舞足蹈,来不及呼唤妻子 等歌唱完了,才匆匆对婉冰说:
“元浪点歌给我贺生辰,他原来去了美国。”
“是真的吗?你没听错吧?”
“没错,播音员还说他的生活很好,叫双亲放心,所以不敢写信。”
“他又不会英文,怎么敢一个人到美国?”
“我也不清楚,他还说希望早日和我们相逢,是什么音思?”
“当然不是说他会回来啦!大概暗示我们出去吧?”
“对,你说对了,他必定是这个含意,再呆下去,子女全没有前途,生命安全没保障。华裔又是他们的眼中钉,有个运动,又必定倒霉。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三十六著走为上著,你怎么想?”元波关掉了收音机,从元浪点唱里,引起了他从未思考过的问题。
“老二是单身汉,我们拖男带女,明明只有三岁,那条路也不容易,危险性极大,是不是?”
“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不冒险,留下来,后果是怎样呢?” 元波对这个土生土长的第二故乡本也充满了留恋,新制度也曾经使他迷惑过。但这两年半,目睹耳闻的事实,使他对越共的残暴阴险真面目看清了,也完全惊醒了。更坚信了历史故事“苛政猛于虎”的记载,他的信心全飞走了。
“这种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决定,不能冲动,谋定而后动,我也没说不走嘛!”
“好!我早知你深明事理,夫妇同心什么事都好办了”元波高兴的一把搂著太太,情难自禁的吻著她,心里憧憬的又是 一个阳光普照自由的乐园。这个乐园,究竟在哪儿,他一点方向感也没有,只相信能够冲破铁幕,海洋的尽头,必是人间天堂。
翌日、他先到郡公安局报到,这半年来,每周都要去报到一次,释放后在行动上仍要受地方政权的管制。这种监视要多久元波不知道,他只明白,若不报到麻烦会立即降临。
报到后、郡公安值日官在他的品行手册上盖个印章,填上日期,签个字,就算了事。虽然简单,但地方政权就知道你这个人没有远离住所、还是乖乖的呆在原居地。
离开公安局,他就到元涛那儿,见过父母。把元浪的消息通知他们,他妈妈即到神龛前烧香,向祖宗神明谢思。
元涛坐在那儿,元波面向他,对他说:“你有没有想到走老二那条路?”
“没有、爸妈年纪大了要我照顾,况且、这里好吃好住,”他笑嘻嘻的挨近元波耳边轻轻说:“安南妹又美又温柔,舍不得啊!”
“说正经的、如果你有决心,爸妈到我那边住。”
“我们老了,不必为我们这对老骨头烦心,你俩兄弟都要认真打算,走为上策。”他父亲开口用他一向自信而坚定的语气说。
“爸爸、元涛和我一起行动,无论如何我们也不放心留下你们。要嘛咱们一块走,不然我们兄弟留下一个陪伴你们。”
“老了,去不去都没问题,你们俩兄弟不必以我们为念;可以一起的话,我们拼著老命奉倍,不能全家都走,你们要当机立断啊!”
“大哥、你和大嫂侄儿们先去,我留下陪爸妈,一起行动太危险了,成功当然好,但也容易一网成擒,到时、叫天天不应了。”
“阿涛的话有理,不过、谁先谁后不是现在争论,先找门路, 再看情形,有决心先后不是问题。”老人微笑著为他们下结论。
“是的爸爸。”
闲话结束后,元波离开时,弟弟跟著出来,在门前对他说:“大哥,明雪已经走了。”
“去了那里?”
“不晓得,是你去见他以后,没多久,我再去时,才发现她已离开。也许,她不愿再见到你?”
“她会去那里呢?”元波心里茫然的,有份说不出来的惆怅。
“来来去去还不是那种地方。”
“真的要偸渡,倒很想和她说再见,问问她是否也想走,我答应张心代他关照明雪,没做到真是愧对朋友。”元波自言自语,心事重重的深锁眉头。
“算啦!她有意避开。相见徒争烦恼。”
元波闷闷的走在路上,元涛的话也很对,相见争如不见,此时此地,再见面情何以堪呢?而且、何以对婉冰呢?
回家心情落寞的扭开收音机,听到澳洲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恰恰在报导新闻,说起一条小铁船直接在汪洋上和风浪搏斗,经过了十九天的艰苦航程,全船七十多人终于平安到达北部达尔文港 。这批侵犯澳洲领海,非法入境者因为是难民,受到了澳洲政府人道的收留,这艘小船的到达轰动了澳洲全国。这个消息也使元波更坚定了逃亡的决心。
越南在越共统治下,黎笋集团梦想成为东南亚新霸主,战后全面亲苏,和中共反目成仇,在北方要陈兵多师团以防中共挥兵南下。西南方则沿著柬越边境,和波尔布特的柬共日夜争战。中原高地里南越复国军更时刻出击 ,同时面对三方敌人,兵燹连绵,军队疲于奔命,民不聊生。全国精壮都投在战场上,以至全越经济崩溃。越共用其恐怖独裁手段镇压人民,对南方城市,他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失败后,为了迫使城市人民走向生产单位,越南构想了一个全面改变国家经济的方案,立即如火如荼的吹嘘著推行。
这个方案就命名为发展“新经济区”,街坊会、各级各区的党委会,在竞赛的向党报功。全南方都忙著说服人民去自力更生,(仿佛南方人民都是寄生虫
?)一时间、开会又风起云涌。报纸电台一片形势大好,对于天方夜谭式的“新经济区”,便成了点石成金的法宝。似乎只要到了那荒芜的水田,人民便立即富庶走来?
在城市没职业,没收人的贫苦大众,呆在城市也是一条死路,就幻想著党的指示,期盼能够从此翻身,改变命运?
第十一郡的穷人特别多,第一批报名去水草平原开荒的有二十五个家庭,老杨一家七口也榜上有名; 出发的当天,欢送队伍里,敲锣打鼓,上了军用运输车的人受到了英雄式的敬礼。大家笑容可掬,老杨和元波握别时,轻声的说:
“反正左死右死,穷人先死,我无路可走,再信他们一次,你保重!”
“你也多保重,可以写信,把那边的情形告诉我,好吗?”元波紧握著这位老芳邻的手,并把一个红包,里边放了一百元,交在他的手里说:“不成意思给你顺风,不必推辞,你子女多,什么都要从新开始。”
“谢谢你,我会写信给你,生活改善,我出堤岸一定来探望你们。”
杨太太和婉冰相拥的各自流泪,阿美和老杨的女儿手拉手,有说不完的话,这一别,后会无期,那些在车上笑的,必定是了无牵挂的人?
几次三番,元波差点忍不住要向老杨说,他将来出堤岸时,也许相逢无期了。面对这位好邻居,不能说真话,心底总感到很难过,也很对不起他,但这关连生死的秘密,真是不可造次呵 !
车队启程,尘土飞扬,车上的人都挤到两边挥手,没有人知道前面是条什么路,元波夫妇和女儿也向车上的人挥手,识与不识,一起祝福他们好运。
运动城市的居民到‘新经济区’劳动生产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成了一项战役。(共党无论搞什么运动,如排华、打倒资产买办或换钱全当成战役,排山倒海般的用战争方式进行。)打开报纸,扭开电视,所报道所鼓吹的,通通是新经济区的奇迹神话。
每一郡每一坊的地方政权,天天都组织了访问队,逐家逐户的进行游说,再加上那许多美丽的描写,许诺。对于日子难过的劳苦大众,毕竟是条很诱惑的出路。所以、每天就有不同的车队奔向不同的‘新经济区’、落实了党的政策,全国浸沉在一片无比光明的前景里。
不到几个月,几十万胡志明市的人民,都已抓紧铲锄,自立更新的参加了劳动大军。照说去了几十万人口,城市应该较前冷清?可是、从北越涌下来的干部军民,很快的补充了下乡上山的那班原有居民。故此、白天的城市还是极挤拥,夜里的街道,仍然是黑暗而凄清 。
老杨没有寄来片言只字,几个月过去后,在元波几乎淡忘了后,‘新经济区’ 的神话像吹涨过度的气球,出乎意外的爆开了。在六省车站,安东市车站,天后庙,本头公二府庙广场,这些地方给愈来愈多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幼作了临时栖身之所。他们向施舍的路人说,是从‘新经济区’偷跑回来的,消息很快的流传著,没多久‘新经济区’这个名词就从遍地黄金一下子变成了令人闻之心惊的人间炼狱。
老杨憔悴消瘦的也回来了,杨太给毒蚊咬到双脚浮肿,发烧发冷,无药可治而死在水草平原里。他们的家已给共产党员接收了,他和几个儿女分散投靠亲戚。那晚他单独来找元波,元波没想到是他,请他进屋,一边拉上铁闸,一边问:
“什么时候回来的?”
“三天前、我们上当了。唉!阮文超讲的话一点也没错:“别听信共党说些什么,要看清共党的所作所为”,这两句话已经成了真理,你明白吗?”老杨声音激愤的说。
“明白、全南越的人民都明白。是不是当我们明白了,已经太迟了呢?”
“是的,像我们这样,把太太的命也赔上了,家破人亡、我真的对不起她和孩子们。”
“老杨,别太自责了啦!事已至此,难过也挽不回,究竟那儿是怎样的情况?”
“我们被载到迪石省后,再转小船沿湄公河支流进入了水草平原的荒谬地带。没有屋宇,四面都是野草,原来、什么没有准备,乡公社每户赠送一枝铁锄,三个月的米粮和杂粮,把我们抛下就由得我们自生自灭。没有学校,市集,没有医疗站,我们这些城市人一下子过著野人般的原始生活。
首先要动手烧草除草,才自建帐篷,等到粮食完了,种下来的玉米,瓜菜全长不出来,地质是醎的。到达当天,我们就知道上当了,但已经无可选择,唯有忍著泪和天地搏斗。希望找出一条生路,等到我太太死去,一些邻居的孩子也牺牲了,大家才决心逃回来。”老杨娓娓的把自已经历的事讲出来
“是谋杀,骗南方城市居民进地狱的一种方法,你有什么打算?”元波气愤难当,来回踱步,仿佛受骗的是他自己。
“能有什么打算呢?过一天算一天。”
“市面百业不振,民不聊生,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很难找到工作、你可以再卷些烟到街边摆卖啊!”
“我也想过了,可是我连那点小本钱也没有。”老杨低垂下头,声音也沉下去。
“你等等。”元波说完跑上楼,再下来时把手上的钱递给他说:“这里一百块钱,先拿去买烟丝烟纸。”
“你这样帮忙,你的大恩我会永远记著的。”
“老街坊,何必说那些话呢!”
送走了老杨,元波心里翻滚难安,怎样也没法想像,‘新经济区’这个名词代表的是恐怖绝望和死亡,也想不通为什么一个政权可以无视于百姓的生死?把老百姓的生命作为他们的试验品,新经济区的计划完全失败后,整个沸腾的运动也停止了。
民间穷苦大众,以前都对越共存著再生的盼望,把他们看成了救星;现在也完全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对这个以谎言取天下的极权制度,大家都深恶痛绝。久而久之,这种反共情绪变成了消极的抵抗,人人没心工作,对政令阳奉阴违,走私买卖的,有了钱就大吃大喝大赌大嫖。日子变得只有今天,而明天,是一个渺茫的未知数。活著不存在任何希望,人!变得和动物没有分别。
而元波和许许多多在西堤的华人一样,(西贡堤岸简称为西堤。)如今、把希望寄托在海上寻觅自由的构想里。元涛和他们一起两次到了头顿渔村。申请路条的理由是寻找可耕地,准备下乡务农,在这些名目下当然也是花点应酬,始可顺利拿到离城的许可证。
看到了这几艘破旧的小渔船,只有十八公尺长,四公尺半宽阔的面积,想像一百馀人挤迫在上边的可怕情形,元波的信心动摇了。这类只适合于在内河及沿海航行的小船,怎能在汪洋的风浪里航走呢?完全没有把握的投注,真无勇气去冒险啊!那些可以平安到达彼岸的人,除了命大福大,那份视死如归的精神,元波真的深深感动和敬佩。
还没有深入去探路,日夜都为了能早日偷渡而兴奋;等真正见到了渡洋的简陋工具后,代之而起的是恐惧和失望,情绪也变到落寞和低沉了。
这段日子,无聊起来,元波常常独自在鸣远学校六叉路附近的小食挡,要碟花生米,来几瓶33啤酒或糯米酒;元涛也偶然陪他来,不为什么的喝著闷酒。 一醉解千愁,回到家、微醺里倒在床上,是很容易一觉酣睡到天亮。婉冰容忍著,她了解丈夫此刻的心境,不想给他什么压力。第二天清醒度,他知道自已是在逃避著,不敢面对而又深心寄望的唯一可行的路。
那天、他没有醉,电台播出了雄壮的军乐,然后,就宣读了一篇文告。好像这种文告是古代皇帝圣旨,一发布后,人民除了完全首肯外是不该有任何怀疑的,越共的头子们必定如此相信著。文告洋溢著种掩饰不住的兴奋: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民军队,兵分四路,从河先省,朱笃省,茶荣省和西宁省的柬越边界,在战车坦克飞机强大火力的配合下,浩浩荡荡的为兄弟的柬埔寨人民解放他们的国家,解救水深火热被魔鬼集团恐布统治的柬埔寨广大人民,法西斯杀人恶魔波尔布特兵败如山倒,在正义雄师的进攻下已溃不成军的退出首都金边,逃窜到泰柬一带,柬埔寨的人民已组织了新政府、、、、、”
正式侵略的行动,经过精心编演,文告的词句如听后未经思考,听的人是会感动的。越共的霸主野心,已赤裸裸的呈现在挥军入柬的事实上,元波忘了自已的处境,居然为东南亚的其它地区的危局担心。
战争仍旧进行著,大批的柬埔寨难民分别由沙沥,朱笃,河仙,茶荣,西宁,鹅油这些边界省份拥进了南越,辗转到西堤来的也到公园,学校操场,庙宇
暂时栖身。
这些不幸的难民,有越南人,有柬埔寨人,也有说潮州话的华侨,他们看来都是又黑又瘦,衣衫褴褛,在苦难的岁月里,挣扎求存的痕迹都刻在五官上。他们把在柬国这几年的恐怖遭遇向过往的人哭诉,波尔布特像条凶残恶狗,把柬埔寨全国人民迫进了鬼门关,疯狂的杀戮了几乎占了人口半数的几百万人。他们娓娓道来,没有愤怒,没有怨恨,听众却毛骨悚然,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呵?人间,真会发生如此凄惨可怕的事吗?
元波从讲越语的难民听到的和讲潮州话的难民听闻的故事大同小异:黑衫兵,(柬共未成年的兵士多穿黑衣)用锄头敲人民的后脑,一锄一条命:集体活埋,乱枪射杀,全国变成了集中营,人民生不如死的成为奴隶。在二府庙的那堆新来的难民所说的和六省车站先到的难民讲述的也没有分别,元涛也好奇的去听这些恐怖的惨剧,和元波所知的印证,他们得到的结论,那是真的事实。
元波把这些听闻告诉父亲,他父亲说:
“比较下,印支三邦,柬埔寨的人民算是最悲惨了。如果越共也这样,我们在越华人也不知要怎样死才好呢?”
“您的意思是他们亲苏,反而对我们客气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们亲苏,在此华人变成了中国可以利用的工具,越共如用野蛮手段对待我,中共就有借口。上次的撒侨闹剧不是已经证明了。但越共如亲中,同志加兄弟的情谊就永远存在,越共想怎样整顿华侨,中共绝不会干涉,这才算得上够兄弟啊!波尔布特便是这样大杀华侨,中共那有抗议反对呢?明白了没有?”
元波点点头,终于明白了,经父亲点破,再细细思量,一股浓浓的悲哀涌上心头,做中国人,做海外的华人,原来都是那么不幸。他父亲在吞吐的烟雾中,又开可说;
“越共投鼠忌器,但并不是说对我们就会安好心,不过,他们做得较聪明,什么运动战役也连同南方人一起来。但骨子里还是千方百计的要排除华的,用什么方法,只好等著瞧了。
“爸爸,元涛说近日西堤的客栈忽然都住满了从北方来的大批干部,他们成群结队的到处招摇,我碰到了很多,有男有女,又不是军队,市面也热闹多了,大家都猜不出这班人的任务。”元波把这个近日出现的情况告诉父亲,他对父亲的判断都很信服。
“一时三刻也没法清楚他们的来意,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场新灾难了。”
“可能是再换钱,南方解放阵线已经给北越吞吃了,南北统一后,没理由分别用两种钱币呵!”
老人抽出另一枝烟接上火,把旧烟扔掉,喷口烟才说:“是或者不是,不用多久就会知道了。也不必太担心,要来的逃也逃不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能够像阿浪,就不必再受精神拆磨了。你兄弟一天还在这里,我一天就不能安心。”
“爸爸、生死相关的事,急也急不来,我们看了几条船,都不很理想,若出海,沉没的可能性很大。心里真的不敢决定,如我是独身汉,就不必想太多。”元波回答说。
“我明白你的想法,记得机不可失时,就要拼一拼,错过了,将来终生遗憾。”
“是的,爸爸。”元波很想问,什么时刻才算是好时机呢?逃亡!每一时刻都充满危险和被追捕枪杀的可能。为了自由,追求幸福的生活,许许多多的人都在企盼用性命作一次赌注。下注前的准备工作,千头万绪,只要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完了。失手被捕的人,财产被没收,还要送到劳改场四、五年;等到出狱,已成了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乞丐,可以说永无超生之日了。这残酷的事实每天都在发生,也就成了元波的踌躇与徬徨。他担心害怕的倒不是自已的安危,而是妻子和几个未成年的儿女,他们的命运全操在自已的手上,那份无形的压力,使他在微醺里格外向往元涛那样的单身汉。随时可以押注,输赢都是自身的事,就因为肩膀上挑著全家的重担,他不得不婆妈,不得不格外慎重。
这些困扰一直使他几个月来坐卧不安,基至借酒消愁,直到越共一个排山倒海的新战役向全南方华人发动后,元波已经没有选择的馀地了。
本文由看新闻网转载发布,仅代表原作者或原平台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立场。 看新闻网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或有适当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