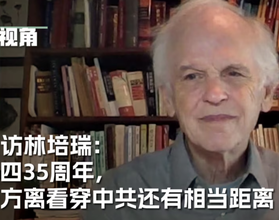我是熊焱,我是美国纽约州联邦国会众议员第十选区的民主党参选人,我有27的军龄,33年前我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参加过那一次伟大的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
《那一晚,我不知道如何止血》作者:熊焱
“救护车!救护车!伤的年轻人血已流尽。那个晚上的记忆总是自动浮现,枪声与兽行在北京的夜幕中,四百年未曾出现,五千年埋在石头底下的人都冒出来看北京的屠杀看年轻人,看着流血的年轻人。祖国啊,那一晚,我不知道如何止血,到今天我的心,即使不是阴天也隐隐作痛。”
大屠杀嘛,政府开枪,动用政府军屠杀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对我们的人生是影响多大。对一个个体的人是这样,对一个民族何尝不是这样呢。
八九民运六四事件,爆发于1989春夏之交,由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起的示威抗议活动持续了近两个月,波及全国。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中国军队对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示威集会进行了武力清场。熊焱,八九学运北京高校学生领袖之一,当时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
熊焱1986年从湖南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研究西方法律哲学。
当时的北大呀,还是相当的宽松啊开放啊,大家都知道北京大学有学生运动的传统,所以我们进去以后,86年有一次,88年有一次,然后89年又是很大的一次。所以在那个时代,好像每个学生走上街头,好像是件很光荣的事情。
哎呀这个是最感动人的,不是我一个人啊,几十万上百万啊,市民学生群众工人,包括中国的各界人士在天安门广场,不是一个人啊,他们都在那里哦。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学生们真诚纯洁善良,想要为这个国家做点事,何况那个时候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学生们社会各界,希望有一个政治体制的改革跟上来。
当时虽然中国是相对开放的,但是那些老的知识分子,还是不敢说话的,听到北大三角地的广播,天安门广场的广播,那些老知识分子戴眼镜啊,激动地悄悄地握着我们的手(说),好啊,好啊,好啊,时机到啦,好啊,好啊,你们有希望啊,我们有希望啊,好几个人都这样对我说啊,那些老知识分子,这个忘不掉。我流眼泪,好啊,你们了不起啊,因为他们有几十年的内心的积累嘛。碰上八九民运这一代年轻人无所畏惧走上街头说要民主自由人权宪法改革开放,反官倒反腐败,这是好事啊。
我们那是以火热之心,以纯净之心要为国家做好事为社会做好事。但是我们年轻啊,我们并不知道事情的复杂性,而且群众的学生的运动是不可控制的,虽然我是学生运动的发起者。但是到了中期后期,也并不见得我就能够指挥啊,不能啊。
自5月13日起, 学生们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抗议,要求政府改变《四二六社论》中有关八九学运是“动乱”的定性。
5月14号第二天是戈尔巴乔夫(前苏联总书记)访华,要从天安门广场进去,学生们、临时凑起的学生们,或者学生领袖代表一起开会,我们要不要撤出广场。
在广场上几经争吵好几个小时,最后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学生应该让出天安门广场,让戈尔巴乔夫正儿八经地从广场进入,决策做出来。
绝食的同学躺在天安门广场,把这个拿起来又睡倒、把那个拿起来又睡倒了,时间就拖到了天亮了,所以后面的报纸报道啊,学生们占据天安门广场啊,和事实是不相符合的,但是群众运动谁能控制呢?群众运动谁能够知道真实的状况呢?
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等官员与11位学生代表进行了面对面对话,李鹏要求学生终止绝食抗议,学生要求政府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的、不是动乱。熊焱在现场向李鹏提出了问题。
熊焱与李鹏对话:“这样一场运动,不管政府方面及其其它方面是否承认它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但是历史会承认它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但是为什么同学们特别地需要政府方面及有关方面承认呢?我想大家都是表达这样一个愿望,想看一看我们的政府到底还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政府。”
光荣,说不光荣是假的,同时但也是表示哎呀毕竟死了那么多人,我们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回过头来说是不是还可以把那场运动做得更好呢?比如说对话的时候继续对话和政府的沟通加强。1989年的民主运动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运动。当然市民参加啊都参加,但是中国的主体的精英知识分子并没有真的出来,他们有经验,他们有些智慧啊。在89民主运动对话的时候,要是能够更多地倾听来自知识分子的声音啊,某些政府部门官员的声音啊,和其他和我们对话的这个人的声音,如果稍微多听一听,可能可以改变一点方向。虽然我知道历史复杂,不可能按我们想象地去(发展),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有这个努力嘛。第二呢介入了党内高层的纷争,我也不具体了,或者以赵紫阳为首的这一派和邓小平为首的这一派,他们有党内的纠纷,这个我们学生是不知道的,所以学生被夹在中间。最后呢?没有一个真的健康的理性的有强大的力量,出来引导这个学运,学生你能做什么。除了火热的心、纯洁的心想要做点贡献以外,他没有力量啊。当然你能责怪谁?历史可以责怪谁呢?不能责怪谁啊。
5月20日,中国政府宣布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从五大军区调动兵力开赴北京。6月3 日,李鹏会见军队和北京市领导人,会议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必须果断采取强硬措施扭转局势。6月3日夜间至6月4日凌晨,军队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武力清场,被称为“六四事件” 。
我还真抬过尸体。所以这件事情对我还是有些影响的。抬过尸体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年轻的学生,不会知道止血,看到他流血,把他抬到自行车上进到医院。虽然不是我们杀死他的,但是我们那个负疚感是有的,那样的镜头其实是忘不掉。我们把他抬到自行车上,他失去了平衡。中途还从自行车上掉下来过,掉到地上,那个我现在我回忆不就痛苦吗,又抬上去。到了儿童医院以后,医院里好多尸体躺在平地上啊。
本来我当时6月3号晚上,我正在北京大学,我是不要去天安门广场的,但是我和我的几个朋友一定要去啊,过了木樨地还要往广场前进啊,还要匍匐前进啊。我们希望被打死,在那个时刻。我们希望“嘣”把我自己打死。在那个时候人们已经没有恐惧感了。
六四是个悲剧,是个民族的悲剧、人类的悲剧,要避免那样的悲剧,那是我们这一辈子应该做的事情,包括人类的、其它国家的、世界的。
6月4日,熊焱跟他的导师张宏生通了电话,原定过两天进行硕士论文答辩。
那是6月4号,我在长安街,我就给我导师打电话。我说张老师张老师啊,我知道我的论文答辩是6月6号啊,但是现在我就在这里啊,天安门广场啊,我估计回不去答辩了。
老师是个老教授对我很好,他说不要答辩了不要答辩了,你的论文是写得最好的。不过他也讲,哎呀不是说叫你们不要去嘛。老教授很好啊。
大概到了90年好几个月了,我就因为在监狱里头,后来我就给张老师写信,我说我要翻译一本什么样的书,过了好几个礼拜以后没有收到他的书,是通过另一个老师进来的。因为我老提到张老师,他(监审员)说,我说你和你老师关系这么好吗?我说对呀很好啊,他不知是为什么有意无意透露了一点,他说你的导师已经去世了。我当时就哭了。但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去世的。直到我后来出狱以后,1991年1月24出狱,后来我就知道了,是6月13的通缉令在电视上。然后我的导师70多了嘛,他的儿子告诉他说,爸爸,你的学生熊焱出现在电视上被通缉了,大概半小时以后,他就摔倒在地上就去世了。所以后来,哎呀当然我就很难受嘛。
熊焱1989年6月14日在内蒙古自治区被捕,随后在秦城监狱坐牢19个月。
当时不害怕其实有好多考量。第一我们自始至终还真的没有做什么坏事,只是用言辞表达我们的政治观点,而且我在表达的时候还相当理性。第二,年轻啊,看过好多英雄的人物啊。第三我是学法律的,最多判我3、5年嘛,没有什么很坏的后果啊。
苦了家里的人。刚刚提到我刚刚结婚的妻子,他们是不知道我们在里头怎么样,他们的担心是具体的,我母亲也不知道啊,就这孩子哪去了?半年没有消息死了没有啊。因为据说是半年以后他们才知道我们关在哪里,他们的担忧是一天一天的。
大概是90年,我妈妈去坐长沙的火车去北京,旁边坐着一个相当很有气质的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人,正在看一本读者文摘,其中提到毛主席的那个秘书陈伯达在秦城监狱的生活。他说您去哪里啊。我妈妈说我要去北京。他说你去北京做什么。她说我去看儿子。那你儿子在那里做什么?我妈妈不说话,妈妈指着秦城那个字,那个人立刻就明白了,肃然起敬啊对我妈妈。这个是我妈妈给我讲的故事,所以说我妈妈虽然担惊、虽然受怕,但是实际整个社会对我妈妈非常尊敬,当地的人对我妈妈尊敬啊。
熊焱:“这个照片是我1991年1月24走出了北京的秦城监狱。当时的心态就不一般,我说留个纪念,就到了当时北京颐和园旁边的一个照相馆拍下了这样一张照片。”
我们那个时代,就算我们出狱以后,整个社会都关心我们、关怀我们、也暗中帮助我们,是那个社会的气氛。再讲一个有趣的事,这可以说了啊30年过去了,我出来以后没有证件,也没有身份证,都没有。其中有一个同学,可以说了啊,他说我哥哥是公安局的副局长,可以给你弄个身份证,还真的帮我弄了一个身份证化了一个名,我才有意无意到了深圳,后来就到了美国,意思就是说那个社会相当宽松,令人怀念和留恋,所以我希望我们中国社会都会向前迈进,让人们有自由,有新生活有健康的生活,向前走嘛。
熊焱1992年6月经香港抵达美国,先后攻读英美文学和神学,1994年加入美国陆军,2003年成为随军牧师,2009年获得戈登康维尔神学院神学教牧博士学位。
我是最没有想要来美国的人。
我来美国是太对了,太对了,用基督徒的话说认识了上帝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生活、思想、训练、精神、世界观、价值观全改变了。
熊焱:“美国陆军准尉军官学校,我是这个学校历史上第一任牧师,这是当时一个合照,那些军官啊,那些教官啊,我在这里。”
熊焱的母亲也是基督徒,未能为母亲祷告一次成为熊焱人生的一大遗憾。
我觉得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是我妈妈。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亲切好到什么程度?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初中吧,我妈妈还给我洗脸呢,哈哈,我妈妈是个非常亲切的人。我妈妈是个民主作风人士。但是遗憾的是,的确她躺在病床上我没给她梳梳头啊,给她洗个脚啊,为她祷告一次啊。
我妈妈2015年,她从三月份开始病危到去世的七月份一直是躺在病床上的,但是现在有手机啊,人们朋友们时不时给我发个母亲躺在病床上的照片。你说我不看?是我妈。你说我看了,看了我久久不能平静,所以那种痛苦是很痛苦的。哎呀,据说我妈妈躺在病床上快要去世的时候,人们总是说这是你的儿子熊焱回来了,我妈妈的眼睛就睁得稍微大一点。
一个女牧师年纪比我大一点,她就问到一个问题。她说你妈妈躺在病床上,她疼不疼啊。那一句话使我立刻泪奔,因为我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就不知道当一个年老的八十岁的人躺在床上,三五个月不能动,或者说要去世的前奏,她在肉体上的疼痛是个什么状况。
2015年7月,熊焱母亲病逝于湖南,当时熊焱在Fort Bliss美军驻地。
我哥哥来了一个短信,母亲去世,我们等着排队吃饭嘛,立刻一秒钟,我这个心就乱了,还说吃饭吗?立刻就不行了,我就回到我的办公室给我的上司打电话。哎呀,我妈妈去世了,他们立刻来帮我祷告啊安慰啊。此后,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以后任何时候只要我去排队等什么吃饭什么。哎呀我妈妈去世的那个镜头就来了,这是第一个影响这个挥之不去,好多次好多次,现在还是这样。所以母亲去世以后那就很痛苦啊。
熊焱曾多次试图回中国探望病危的母亲,但被中国政府拒绝入境。
中国有一个文化叫做临终关怀嘛,也不留下遗憾嘛。但是后来我的基督教的思想盖过了我这个普通的情感,就是真的我们的永远相见的好地方in Heaven(在天堂),这个也是
从精神上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毕竟I will see you in heaven(我会在天堂与你相见)。这个是我们真正的思想和情感。
我1992年来到美国,立刻就拿到了绿卡。当时我们的思想只有一个,学好本事包括学好英文,回到中国,继续民主政治改革开放、继续民主政治、社会活动,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拼命地读书啊,拼命地学习啊等等。10年之内没有想要加入美国籍,都是想着如何要回到中国大陆去。甚至我还加入了美国陆军,这是当时有一个思想。学好本事学好军事,还要回到中国大陆,说不定哪一天还能用得上军事的思想军事的经验。
一件事情改变了我,911。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世界发生了质变,军事发生了变化。国家需要打仗,需要前线的牧师,所以我就说如果不成为美国公民,我就当不了军官,我就去不了战场,几经犹豫我加入了美国籍。加入了美国籍以后,我的思想发生了另一个变化。我现在是美国公民了,你说我再回中国搞革命好像也不合适了吧。那么我就要好好为美国服役,要好好来为世界和平做贡献。但是放下了中国的事情没有呢?没有啊,无论是研究、写作,包括研究军事、政治、各种都是为中国的民主改革变形做准备。
熊焱:“希望你们幸福啊,能投票的时候投我一票。”
20年前,熊焱以纽约牧师身份奔赴伊拉克战场,2022年以少校军衔退役后回到纽约决定参选国会议员。
我为什么要出来参选?我是个基督教牧师,是不是,我希望进到国会山,能把上帝的价值观、圣经的价值观能够影响立法者嘛。
第二,中国,不管他经济如何发达、如何发展,物质面貌如何改变,但是始终存在一个问题,国家的权力过大,把社会的力量压制,所以按我们过去的政治学的观点,一旦国家出了问题,整个社会就崩溃,社会没有一种稳定的健康的真实的力量来接管政权崩溃时候的动乱,哇,14亿人民怎么了得啊。
那么在那种危难到来的时候,如果我是国会议员在历史的许多关键时刻,在历史的动荡时刻都是美利坚人民、美国政府做出良好的表率、榜样,来维持世界的秩序。那么如果我是一个国会议员在中国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讲的中国人民大众啊,他们真需要外援的时候,我不可以起良好的作用吗?
还有一个呢?现实的问题。新冠带来的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纽约地铁啊、公共汽车站啊、街道啊,天天发生爆炸的、枪杀的,人们说我们不敢坐火车了,我们不敢坐地铁了。这也不是美国梦。美国梦一定是一个族群和睦团结的梦。华人要强大要健康要提升,还要向不同的族群伸出友爱之手啊。我愿意来做这个工作,和其他人一道。
2022年4月熊焱获得美国国会第十选区众议员参选人资格,他将角逐8月23日的初选。
和我们过去所关注的中国人权民运事业是不是连在一起的?当然是连在一起的。在某种意义上说,600万华裔在美国的命运都赖于一个中国和美国的和平的关系,这个是现实啊,我们设想一下,假如说美国和中国因为什么原因发生了摩擦、冲突、甚至武装的冲突。我们这600万华裔何以自处、我们往哪里放?虽然我们不希望美国和中国有这样的不和平的关系,但是谁知道呢?所以这600万华人来到美国以后,他们是要忠于美国、要维护美国的价值,只要美国强大世界就有和平的可能。因此,我们要极力维护美国的健康的发展,不能走下坡路。
2022年1月王丹发起在纽约筹建六四纪念馆。2月,熊焱卷入一场 “反对建六四纪念馆”的舆论风波,起因于他受邀参加了一个华人社团于2月16日在纽约法拉盛一家酒店举办的座谈会,该会议邀请函写的是“呼吁社区团结、反对族群分裂”。
我说,反对六四于我来说是不对的,那个人(研讨会发起人)也很开通,好对,那我们就开一个座谈会,不提反对建六四纪念馆,呼吁呼社区团结,新冠时期反对族群分裂座谈会,座谈会就是讨论嘛,研讨会,给我发了邀请信,还给我发了邀请函,2月16我们就去了,到了以后,那个大的餐馆里头赫然写着,呼吁社区团结、反对族群分裂、反对什么?反对在纽约建六四纪念馆。
首先这个大标题的出现是我们不知道的,不是我们做的标语,也不知道他要挂上去啊,邀请函上没有说这句话啊,讲好了的。发现以后怎么办呢?当然也是没有经验,但是我们想过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撕棋盘,讲笑话,摔个桌子、翻个板凳、高声大喊一声就走了嘛。但是整个事情这么说要动员侨团来支持我,是这么个大前提来的。第三,研讨,但是上去以后没讲话啊。他说哎呀我们错过了餐馆时间,照片就出去了,当然也是我们没有经验,我也没有在意有这么大的(标语)。后来还在解释诠释,一个照片是不能解释东西的,那里没有我说的一句话呀。当然,你要允许人们骂娘啊。
我们和王丹本身就不是一伙人。不是讲他人不好,他也不错,上次他妈妈去世我还流眼泪了,我在乌克兰他还说你要小心啊,人归人嘛。但是他干的活我们不参加,这个是我们圈子里的人知道,还不用说我现在要参选国会议员,你这明明给我下套。这个和否认六四有关系吗?和否认八九民运青春岁月有关系吗?
我们和王丹虽然都是从天安门出来的,而且是从北大出来的。但我们走都可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道路。美国军队有纪律,要求我们不要和外国政府有任何的经济上的往来,是不是,纪律决定的,所以我就一直在军队里服役,剩下的业余的时间就是自己独立地搞点民主政治、参与点中国的变革啊、写点文章啊,但是实际我这个人不在他们这个群落里头,所以我属于独立大队。
他们的一切的组织活动,我都没有参加过,只是有一次,六四Nancy Pelosi, the Madam Speaker(议长女士南希·佩洛西)邀请我们去的时候,头面人物都要到场啊。
我不参加(王丹的活动)丝毫不是说89年我忘了,我忘了吗?六四的那些惨相我忘了吗?中国未来的民主的变革、人们的福祉我会忘吗?世界的和平我会忘吗?人类的福祉我会忘吗?那是我一脉相承的思想,我可能更努力。
六四的很多重大活动我都参加过,我2009年回到香港,在维多利亚公园25万人,我是唯一的一个离开中国17年以后,回到香港的学生领袖,发表了八分钟的演说。
熊焱:“擦干死难者家属们伤心的泪水,抚慰他们惨痛的伤痕。”
25周年的时候国会邀请我们见证、祷告我也参加了的。我不参加你王丹的事情,那我就是背叛了六四了?我现在的使命,我要更对得起我妈,我才来竞选国会议员,我要更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我才来当选国会议员,我要更对得起中国的未来,我才来当选国会议员。
一个联邦国会议员的侯选人,美国的选举,它会高度关注。一方面不允许有任何人对我侵害和伤害,另一个它也保护不失脚啊,不失脚、不能违背美国法律。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合规合矩、中规中矩啊,还有比这个更严格了没有?还有比这个更清楚了没有?
2022年3月16日,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披露,来自中国的特务试图破坏熊焱的国会议员竞选。
司法部的文件公布了以后,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但是你说生活当中有没有蛛丝马迹呢?有。十一月底的某一天,我和朋友约好开车去印第安纳见朋友,凌晨三点,正好在我开出来的那一秒钟一辆车开进我的parking lot(停车场)。哎,我说咋回事呢?凌晨三点呢,他是不是下夜班呀怎么,就没有多想,总之就是很奇怪嘛,太巧了嘛,一秒之间,然后他看到我开出去,他就退回来就停在我房子的旁边,我就经过他的旁边,我就想看看,那个人低着头,那件事情我就记住了,后来我还写在我的日记里头。
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3月9日,熊焱奔赴乌克兰战场,为和平祈祷。
我到了那里后,我就真的感觉到儿童时候我背的唐诗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个时候是春天啊,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四句诗还有,立刻变成活生生的场景,深深地进入我的心灵世界。乌克兰人民在战争的阴影的笼罩之下,他们国破山河在。其中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在教堂的旁边弹吉他,我去的时候三月份,乌克兰还是天气比较清冷的,那个吉他的声音,我虽然记不得是什么曲子,清冷、幽怨、低沉。结论是和平好啊,不打仗好啊,国与国之间和睦团结好啊,一旦国破何以自处。
在某种意义上说1989年这场运动过去以后,大浪淘沙。把我这一代人淹没。很多人鼓励我,熊焱啊,你是仅存的硕果。你要对得起死去的亡灵,你要对得起你的母亲,你要对得起中国的未来,你要在美国的政坛上占一席之地。为世界的和平做贡献,为人类的未来做贡献,为2000万华人做贡献,将来若有机会还要为中国的未来贡献。
现在我今年57,中国生活了28年,在美国生活了30年,我现在晚上做梦,基本上99%都是中国大陆的储藏的信息和记忆出来。所以中国,你怎么能够忘记呢?
我有一个极好的家庭,上帝赐我7个孩子,我给他们的取名叫北斗七星。
我不是有两次婚姻吗?我过去20年和我前妻结婚,我每篇文章都有前妻的影子在里头。美国陆军的生活使我们的婚姻生活极其的艰难。因为我们每2年都要流动一次,我在美国流动了17次,当我的孩子们要上初中高中的时候,他们不能流动,所以带来很多生活的困难。这是为什么总司令说,我们感谢那些阵亡的将士,我们还感谢那些现在服役的将士,因为他们做出的牺牲是别人不知道的,包括家庭的牺牲。
叶落归根的这个概念我已经没有了,我死了以后,我如果愿意的话,我就埋在这个旁边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初衷不改,理想更加明天,虽然头发渐稀,理想不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文由看新闻网转载发布,仅代表原作者或原平台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立场。 看新闻网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或有适当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