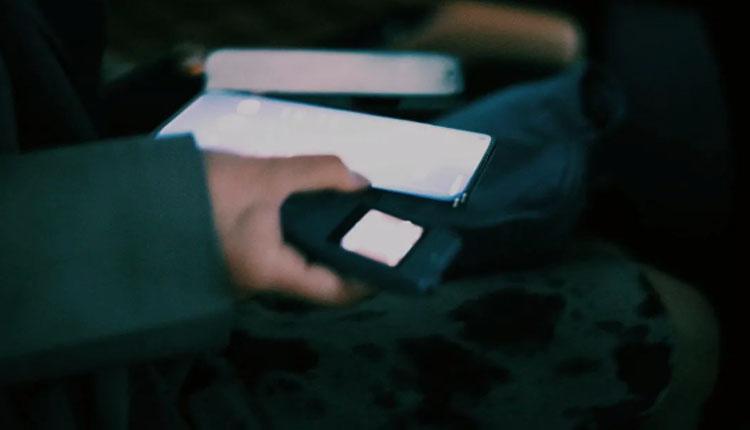前幾天有朋友問我,最近怎麼沒有發非虛構了。我回了一個「哎」,然後什麼也沒說。
其實我沒說的,有很多。
我在一家雜誌社做專題編輯,這份工作讓我有穩定的收入,但是理想很難談起。業餘時間,我在做野生記者。所謂「野生」的意思是,我不隸屬於任何機構媒體,只能供稿。雖然謝謝幾位編輯老師,我的文章能夠在一些媒體上發表,但可惜的是,我沒有記者證。
以前在電影媒體工作,採訪的都是演員、導演、編劇之類的電影工作者,很少人拒絕採訪,也從來沒有人要求我出示記者證。但當我開始做一些社會報道,一邊是官,一邊是民,記者證就變成了很必要的證件,你可以理解為「通行證」。
我沒有這本「通行證」的原因是,只有進入官方認可的機構媒體工作,才有資格考取記者證。所以嚴格意義上來說,你要說我是個「假記者」,我也無從反駁。
今年七月我去農村採訪環境污染。那個喊我過去的村民開了輛車,冒着暴雨接上我。在路上,他還接上了另一個有證的記者。那個前輩很有經驗,路上聊着他過往跑突發新聞的刺激經歷。雨停了,村民很熱情地帶我們去吃飯,席上聊了很多。飯吃完了,他突然拉着我問,你有證嗎?他的語氣很堅定,無從迴避。好像如果沒有證,我們的緣分就到此為止了。
我只能拿出一張工作名片,上面寫着英文,看起來像個外媒。但我必須向他解釋,我要寫的文章並不發表在那裡,這張名片其實沒有什麼意義。對方會投來狐疑的眼光,很勉強地對着我的名片和身份證,拍了一張照片。
這還不是最沒有底氣的,如果我走進機關單位,告訴他們我是一個野生記者,等待我的往往是被拒之門外的命運。再進一步想,如果因為我的調查動了一些人的蛋糕,他們以「假記者」為名逮捕我,向我約稿的機構媒體,也只能遺憾地告訴我,很抱歉,你不是我們的正式員工,我們不能保你出來,所以不要冒險。我曾向一位媒體前輩請教,如果遇到危險的情況怎麼辦,他教了我一套偽裝自己的辦法,我不打算寫出來,因為聽起來像spy。
當然有資格向機關單位發問的程序,遠不止一本記者證。就算在我所在的雜誌社,有正兒八經的理由需要採訪機關單位,也只能郵件寄送採訪函或者發傳真。我寄過一次,整整兩個月靜靜地等待石沉大海,從此我沒有再試過。
鋪墊到這裡,我想大概你可以理解,從發上一篇文章到現在,差不多三個月過去,為什麼我手裡的兩篇文章難產了。當然也有我個人的原因,政治抑鬱久了,會有那麼一段時間不想看任何新聞,不想繼續手裡的事。一天天機器人似的上班下班,像《摩登時代》裡流水線上的工人。難產文章的採訪對象偶爾還會給我打電話,告訴我事件的最新進展,我也會跟一跟,然後慚愧地避而不談什麼時候發稿。
做這份工作,我常常背負着道德負擔,它有時拖累我。我遇到過很多次採訪對象問我借錢,最開始幾次我會傾囊相助,可是也遇到過手裡沒有餘錢的時候,我很慚愧。一旦沒有再借,慚愧也漸漸消失,此後的很多次,我即便有錢,也不想借了。也有的時候,我答應採訪對象,一定會以朋友的身份再次拜訪,卻遲遲沒有赴約。可我明明有時空閒,也寧願做別的事。
我的朋友勸我,金錢和時間不是看實際情況,而是看你有沒有去挪用,如果沒有,那你就是沒有那個金錢和時間,就別勉強了。我想她說的對,但這份慚愧依然會時不時地冒出來。我認為,我不是個道德多麼高尚的記者。
道德負擔也有時轉移到了別的地方,它會激勵我。七月我寫的文章《手持紅碼,流浪地球,被驅逐的俄羅斯華人》不幸被原來約好的媒體撤稿了,我加了數十家媒體老師的微信,心裡想着一定要把文章發出去。「我不能辜負被採訪對象的期望」,我對他們說。這樣的情緒,採訪的人越多,疊加得越多。
八月我去西寧做電影節的報道,那是我的興趣,也是我工作的單位要求的本職工作。那時候我幾乎到達了生理極限,連續八天每天採訪看片,凌晨四五點才睡。在影院裡,我錯失了七個電話,等我再打過去,無人接聽。後來我才知道,電話來自一位我曾經採訪過的大爺,當時情況緊急,他的事急需馬上前去報道,可我挪不開身,從此那個電話再也接不通。這件事讓我後悔了很久,我不知道再來一次,我會做什麼選擇。如果我去了,真的可以幫到大爺嗎?我不知道。

我們記者不是律師,不能解決民間的一切苦難,這是一個記者朋友對我說的話,我想他說的有道理。但是再看一遍那句話,律師其實也不能安撫所有苦難,有些事情是律師做不到,但是記者做得到的,或許。
二月我採訪過一路奔逃到羅馬尼亞的烏克蘭女性難民(《逃亡的烏克蘭女性,和幫助她們的羅馬尼亞人》已刪),聽見過話筒那頭傳來的槍聲(《在烏克蘭,消失的動物聲音》),很努力地爭取他們對一個中國記者的信任。我吃下了一些國與國之間的不理解,但我很難消化,拋開這些人們對「記者」這個身份的不信任。對記者的警覺和誤會是我常常遇到的困難,「替誰說話」,以及「說話有沒有用」,成了我為自己爭取採訪機會需要回答的主要問題。
我很難忘記一位女性的眼神。她是一個至今未破案件的受害人家屬。站在當年的命案現場,我與她面對面交談,我對她表達了打擾的歉意,也自認為很真誠坦率地告訴她前來的目的。但當她問我,你一個沒聽過的媒體記者,能有什麼用的時候。我愣了幾秒鐘,然後我舉了唐山打人事件的例子,我問她還記得發視頻的號叫什麼嗎?但是所有人都記住了那次事件,它被討論了很久,有人因此受到懲罰。她的眼睛裡出現短暫的光亮,但很快又暗淡了下去。你就當沒見過我,她說。
她不相信,我失敗了。
離開她的時候,我安慰自己在那半個小時裡,我已經付出了所有努力。但也許我還不夠努力。我應該告訴她,去年我寫的一篇戒毒的文章《禁毒老師和他的學生,一場畢生的贖罪》因為毫無懸念的原因被撤稿之後,我發到了只有2000餘粉絲的個人公眾號。卻恰好被人民日報的記者看見,她向我詢問採訪對象的聯繫方式,禁毒老師的故事可以被更多人講述。這樣的情況不止發生了一次,我們應該至少嘗試一下。
我也應該告訴她,雖然我是個籍籍無名的野生記者,但也有幸寫過幾篇十萬加的文章,只要找到時代的共鳴,它或許可以傳到很遠的地方,雖然也不免遇到被刪稿的命運。
但我又有什麼底氣呢?那篇至今難產的文章一直在挫敗我。在我三個月前加入的求助群里,群友不時丟來某某大媒體發布的連接,歡呼一陣過後,又開始抱怨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周而復始,失望和希望之間的間隔時間越來越短,退群的人也越來越多。我有什麼臉去和大家講,這次相信我吧,一定有用。
我從不否認,對媒體環境失望透頂。但我還是相信,我們可以做點什麼,這也是為什麼這行很難做,我還一直在做下去的原因。我對採訪對象說的那些關於「有用」的話從來不假,如果沒有那樣的信念,我又怎麼去說服別人呢?
只不過,我把「一定」改成了「或許」。我有很多個「或許」需要去相信。或許,什麼都沒有用,但我們給予採訪對象哪怕是一點點的安慰和聆聽也是有意義的。或許,我們不可以飛速推動,但可以緩慢前進,哪怕一時倒退。或許,我們會有更好的未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電影少女放浪記
本文由看新聞網轉載發布,僅代表原作者或原平台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立場。 看新聞網僅提供信息發布平台,文章或有適當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