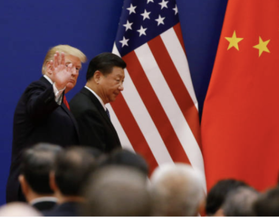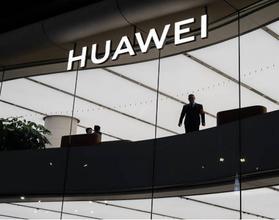他们不懂我们说的话、我们的用词,无法理解我们关注的世界。他们的世界就是挣钱、供小孩读书。
1
临近春节,我回到老家,一个四川的三线城市,与朋友约在新城区的美食街吃饭。我曾经就读的中学就在这里,十年过去,街坊邻居变化不大,让人倍感亲切。
美食街主街建于20多年前,当时市政筹建科技新区,把原住居民动迁到这里。2005年,新区修建新学校,从省会城市请来老师,大力招生。入学名额一部分凭考分录取,一部分作为福利,留给附近三个村的适龄儿童。我是凭考分进了这所学校,不少同学的父母就是周边村子的叔叔阿姨。
我和朋友吃过饭,一边散步,一边闲聊。一个阿姨在旁边听着我们的谈话,凑到跟前。我一下认出她来,惊喜地喊“秀阿姨!” 秀阿姨是同学静的妈妈,她的样貌没怎么变,只是多了不少皱纹,头发白了。冬天风冷,寒暄了几句她就拉着我们走,说“去烤火!”
秀阿姨领我们去了附近的一个小卖部,杉爷爷和几个女人正围坐在一个铁皮桶周围,木柴熊熊的烧着。杉爷爷和女儿开的这家小卖部,不在美食街主街,没那么吵闹,因为是自建房的一楼,不用交房租,得闲时他们在这里打牌、闲聊。杉爷爷是同学奎的爷爷,烤火还有两个阿姨,也都是熟人,一个是同学轩的妈妈,一个是比我们小两届的学妹梓的妈妈。
“我开始真的没认出来哦!”秀阿姨用四川话特有的夸张语调说,“小娃娃又长得快,哪认得到?听她们说到豹妈以前开的干洗店,我才说,肯定是我静娃哪个同学。”
轩的妈妈接茬:“豹妈那个干洗店关了好多年,满打满算就开了4年。”
“所以说嘛,要不是同学,哪个晓得噻?”秀阿姨说。
一群长辈开始询问我们在哪工作、有没有结婚的打算。这些问题让人头疼,我们就岔开话题,问同学们今年回不回。得知轩过几天回来,奎在成都谈了女友,梓今年不回……问到秀阿姨的时候,她把头一偏,气愤地说:“她就莫回来了!我当莫这个女子(女儿)!”
我有些惊讶,问她:“静怎么了?”
静是个学习很厉害的姑娘。初一时,我和静在同一个实验班,初二她升去了更好的实验一班,后来考取了国内Top3的大学。我们初中时关系非常好,我经常到她家玩,到高中就慢慢生疏了。
秀阿姨说:“她现在洋盘(神气)了哦,在大城市挣钱,天天说忙,都不回来。疫情后就回来了两回。”说完瘪了一下嘴。她说的四川土话有一种弯酸刻薄,语气中对静的不满很明显。我和朋友对视了一眼,劝道:“大城市是很忙的,我在上海也经常加班,加到晚上十一二点。”
“过年都不回来,我养这么个女子有啥用?”她有些轻蔑地说。
梓的妈妈劝道,“你快莫这么说,两个月之前人家静才回来了,哪有你说的那么囊个。”
“十一月份她嬢嬢过世!她不回来?她不回来我就不认她了!”秀阿姨说,“而且,回来了才几天?三天!我不信她有那么忙,她就是不孝!”
轩的妈妈也点头,“所以嘛,我不想我家娃儿成绩好,成绩好,考出去,把家都忘了。不然你说养个娃儿爪子喃?不回来,不照顾家里,生病了都莫(没有)人管。我还不如养条狗!”
这话让人不舒服,我反驳她,“但是人家也有自己的生活呀,小孩又不是为了爸妈而存在的,小孩又不是保姆护工。”
“那我养他爪子(做什么)喃?他不给我拿钱,不照顾我,我有娃儿和莫娃儿有啥区别?”轩的妈妈说。她的表情里含着轻蔑,嘴像扁嘴鸭那样平直、紧绷地收缩在一起,显得很严肃。
秀阿姨附和道,“就是啊,我就跟养了个白眼狼一样,一年到头看不到她几回。”
她问我和静有没有联系,“你问她还回不回来,不回来以后就都莫回来了。”
其实我和静联系得很少,但我还是尴尬地应下了这个要求。
2
我拨通了静的微信电话,转述了她妈希望她回去的想法。一个外人进入到他人的家庭关系,我感到有些尴尬。但静说,这不是第一次了,因为她在一线城市,父母不可能追过来,只好向她周围的朋友施压。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问。
我对她们母女关系的印象还停留在初一。当时一个同学请我去她家里玩,不远处就是静的家,我顺道去打了个招呼。静在楼上写作业(自建房有三四层),她从二楼的窗口探头看到我,很开心地说,“我们来玩球球。”她从二楼抛下一个手掌大的球,她抛我接,再抛上去,她接住,如此往复。她母亲就坐在一楼门口的椅子上,看着我们笑。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说起往事,静有些感慨:“你竟然还记得……但你记得我妈当时说了什么吗?”
我努力回忆,大约想起来了,“秀阿姨让你下楼来玩,说在楼上这样和同学玩,不礼貌。”
“对,那天你走之后,她因为这种她口中的不礼貌,把我打了一顿。我第二天都不是骑自行车去上学的,因为痛。”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好一会儿才问:“为什么?”
“因为你是城里人(老城区),她觉得那样丢了她的脸。”静说。
静的父母奉行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当时他们关注静的只有学习,学习不好就是打得不够多。他们和周围村里的人都这样认为,也这样做。
小学时,静跟着村里的孩子在村口看电视,从电视里学到了“隐私”的概念。她买了个日记本,在上面记事,都是一些很细碎的事情,那天学了什么,心情开不开心。对一个十岁的小孩来说,那是她腼腆又澄澈的自我天地。
她告诉父母不要动她的日记本,父母口头上答应了,但依然进她的房间打开日记本。这被静发现了,他们吵起来。她爸提着一根棍子,准备打她。静拼命吼叫,说父母侵犯了她的隐私。听到这话,她爸愣了一下,反问:“隐私?啥子是隐私?”
静说, “就是我有我的东西,你不能碰。”
她爸突然笑了,轻蔑而残忍的笑。他说:“你是我女子!你的东西都是我的。隐私?我看你还说不说隐私!”他扬起棍子打静,静挨了几下打,拼命跑出来。邻居听到动静,远远地喊静的爸爸不要打了,但她爸不听,一直追着她打。
距离她家两公里外,有一个低凹的大湖,湖边有一侧是崖壁,山上的泉水经由崖壁落到湖里。泉水很甜,村里人都专门过来接水。静一直跑到崖壁边上,正好有五六个人在接水。她躲到一个有亲缘关系的奶奶身后,哭着说:“我爸要打我,他一直打我。”
“娘(姨),你莫听她乱说,她自己做错事,我肯定要打她。”她爸争辩说。
那个奶奶卷起静的袖子,看到她手臂上被棍子打出来的伤痕,说:“打两下就算了,你未必(难道)真的要打死她啊?”
她爸命令她过去,她不去。崖壁的路很窄,被几个乡亲挡住,她爸也过不来,最后只能离去。离去前他说:“你最好莫回来,回来我就打死你!”
静很害怕,那天她去了邻居奶奶家住,后来又有几个老人说项,她爸才没有再打。在静心里,恐怖的种子已种下了。
3
初二那年,老师在开家长会前让我们写一封信,向父母表达爱意。静在信里写下了她对父母的爱,同时也写下了父母做过的让她伤心的事,她希望他们改变动辄打骂、情感忽视的行为。
家长会有个环节是让家长读信,静在窗边垫脚看到她爸看了信。家长会后她问爸爸,看完信有什么想法。她爸却说:“你写那么长,哪个看?没看懂!”
静的成绩很好,但过于腼腆,物理老师认为这样会限制她的发展,特地和她爸沟通,希望父母能给她更多信心和支撑,但她爸却说:“老师你莫听那娃儿乱讲,我们还不够支持她啊?我们都供她上学了!她喃们不体谅下我们不容易呢?她一个小的,未必还要我们这些老的来体谅哦?”
物理老师知道没法改变什么,只能算了。
我们关系最好的那段时间,几乎每个月,静都会告诉我,父母的行动如何让她难过得睡不着。2008年地震后我们开始住校,在宿舍楼中间辟出来的半圆形露台,我们常常聊到深夜。她会提起父母做过的让她伤心的事,她也反思,是不是没有看到父母的付出。我劝她要相互理解。
“我尝试理解,他们理念落后,他们不懂我们说的话、我们的用词,无法理解我们关注的世界。他们的世界就是挣钱、供小孩读书,能供到什么地步算什么地步。我拿这些细腻的情感去烦扰他们,是不是‘何不食肉糜’?”静说,“我后来意识到,理解应该是相互的,否则他们只会训斥我,为什么现在不乖了?”
因为静成绩好,她父母觉得“很有面子”,除了打骂,对她的干预倒也不多。后来住校了,静的处境更好些,回到家她也可以借口“我要学习”躲进自己的小天地。
高考填志愿时,父女之间爆发了一次大冲突。她爸不许她报大城市的学校,觉得地方太远,开销又大。那时志愿已是在网上填写,因为无法达成共识,静就按自己的想法填了,心想木已成舟。到最后一刻,她进网站确认,才知道她爸给她改了志愿,她又改了回来。
为此事两人吵了起来。静问她爸,为什么改她的志愿。她爸吼道:“你晓不晓得,一线城市读书有好贵?!而且,在我们这种小地方,你成绩好就真好?你去了那么好的学校,肯定扛不住压力。”
静气得说不出话。她四川话说得不怎么好,她小时就觉得很多人脱口而出的话没有逻辑和道理,为了解答自己的困惑,她读了很多书,但这也导致她的言语体系都是以普通话建立的。她知道她爸的话立不住脚,若用普通话,她可以很好地反驳,但她爸厌恶她说普通话,觉得她“装样”。她只能愣在那里,浑身都在发抖。
她爸见没有反驳,就放软了声气说:“静娃,你就在四川报个学校,过得去就差不多了。你要好好(多好)的东西安?差不多算了,我们家就这样。”
静不知道说什么,只说“反正我把志愿改回来了。”她爸非常生气,又要打她,她直接出门去了朋友家住。
4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周围的叔叔阿姨都称赞静厉害,“静娃一天天不喃们说话,哪晓得考那么好哦!凶(厉害)!”她爸觉得有面子,整日笑着,也不阻挠她了。只是,每次给她拿学费和生活费的时候,都说自己不容易。父母不会用转账功能,每次都要从银行取现金,交给她。她妈看她爸拿出一摞钱,瞪大了双眼说,“这么多钱啊!”然后撞了撞她的胳膊说,“这么多钱嘞,你要记得爸爸妈妈的好,晓得不?”
静点头。她知道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父母一直教育她要感恩,她一直都记得。
后来,静在一线城市工作,她爸说家里自建房要装修,让她给钱。尽管手头也不宽裕,静也给了。对于刚毕业的她来说,那是将近半年的工资。此后她的生活变得拮据,很难存下钱来。有次因突发情况,看病花了2000,一下捉襟见肘,连吃饭的钱也没了。她找父母借钱应急,父母却反问她:“那你的钱喃?”她说因为给了装修的钱,没什么积蓄。父亲却说,“你少怪我们!你自己不好好计划钱!在上海挣一万多月薪,还问我们要钱?你肯定还有钱,就是来哄(骗)我们的。”她只好说“好的”,然后挂了电话。
静先买菜自己做饭,撑了几天,后来只好吃公司的零食填肚子。周末时,她一人躺在出租屋,感到胃部火烧,饥饿感阵阵泛来。后来实在熬不下去,她给一位朋友发了消息,说明前因后果。朋友直接给她打了2000块。她握着手机,缩在床上,哭了很久。
“我以前以为,因为经济条件不好,所以他们对钱很在意,但他们依然是爱我的,毕竟供我上学从小到大。但后来他们开火锅店,经济条件好一点了,情况依然没变,我才意识到,我爸想要的是控制。”静说,“就像他问什么是隐私时的那种口气,我的一切都要由他控制。”
父母的控制欲也逐渐增强,一周打一次电话变成一周两次、每天一次。家里鸡毛蒜皮的事都要告诉她,让她零散地给钱。语气不够柔顺,父母就会说她不孝,跑那么远根本不能回去看他们。
疫情的某一年,她打算回家看看,却碰上四川疫情严重,返乡人员要登记。她和母亲语音聊天时说,准备请年假回去,她妈马上说,“你莫回来,你莫害我们!” 静无力地笑笑,她意识到,他们所谓的想念原来是假的。后来,她没什么大事就不回去了。
有一次隔了两年她才回家,有亲戚来串门。一个表妹阴阳怪气地说:静姐你终于回来了啊,我们盼了你一年又一年,你发达了哦。静想反驳,抬头看了看她爸,只见他面色冷下来,吼了一声:“吃饭!” 亲戚走后,她爸骂她:“你看到莫得?你跑那么远,他们喃们说?我都抬不起头!养了这么多年,养了个白眼狼!”
静意识到,她父亲要的,只是在亲戚面前的“面子”,他把所有压力都转到静身上。
我向秀阿姨求证这些事,秀阿姨的嘴角撇到一边,说:“嘿,她才小心眼嘞,这些事说了无数遍了,一天天就记到这些小事。村里哪个家长没打过娃娃?就她记得清楚。我们小时候哪个没挨过饿?几天不吃饭被她说成啥子样子?”
我感到无奈,只有苦笑。
我很难去责难秀阿姨,他们有他们的限制,金钱上的、心理上的。她说,当初为了让静上学,他们一周就买5元钱的菜,没肉,饭也吃不饱。
过去那一层叠一层的痛苦记忆,让两辈人的理解和沟通变得很困难。离开秀阿姨家的时候,我感觉无力,没办法帮到他们。我能感受到秀阿姨的思念,也能感受到静的痛苦。恐怕只有时间才能解决他们之间的隔阂。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正午故事
本文由看新闻网转载发布,仅代表原作者或原平台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立场。 看新闻网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或有适当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