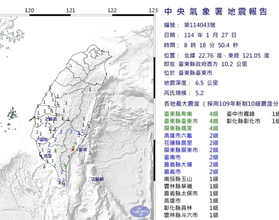地震之后,那些候鸟似的打工者赶回了甘肃省积石山县陈家村。从南到北几千公里,从温润繁华到满目疮痍。
对于这片在四年前才摘帽脱贫的地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强震,显得是那么“不公平”。面对赶来救援、采访的外来者们,陈家村人毫不避讳地讲述着,从前的贫苦以及眼下的困境。
这里曾经的生计是种田、养牛羊,很多人没读完小学,甚至不识字。日子因为外出打工有了起色,村里人这几年越走越远,一直到了东南沿海的电子厂。县里还出台了鼓励外出务工的政策,提供交通补助、给稳定务工的代表发奖金。在一个经济不发达地区谋求改变,“走出去”是自上而下为数不多的选择。
当陈家村大半人外出务工之后,一场地震提醒了年轻人对这里的重要。从搬运物资、安葬遇难者,再到将来的定损重建,都离不开赶回来的青壮年操持。以后怎么办?去留两难。一户户贴着“危房”的院子里,塌落的是打工攒下的十几万积蓄,“家里没钱了啊”,还是得走出去。
一场地震之后,这里依然是那个需要更多关注、帮助的地方。
“我要回去”
今年9月,29岁的绽玉娟第一次出远门,她和丈夫离开大河家镇陈家村,到了2500公里外的厦门,最后站在了一台“和麦子收割机一般大”的机器前。夫妻俩都有些发怵,“这我怎么能干得了?”
他们在一家生产儿童扭扭车、溜冰鞋的工厂打工,绽玉娟的工作是给扭扭车装上按钮,然后送检、填写报表。老员工讲了半个小时,就让她自己上手。她从没填过报表,遇到不会的地方,就跑去拽拽别人的袖子请教。到第三天,她已经像个熟练工,还可以帮帮没太学会的丈夫。
三个月过去,她已经适应了这份每天工作11小时、每月收入四千多元的工作。12月19日这天是绽玉娟的夜班,零点后,刚放下手里的活儿,她看到丈夫发来的消息:村里有房子塌了。几分钟后,又有同村工友打来电话,家里地震了。
她立即拨通了家里的号码,女儿告诉她,一家人都平安,但婆婆40多岁的外甥被压在房子下,家里人正在帮忙救援。
陈家村正在经历慌乱一夜。地震来临时,有村民在睡梦中被晃醒,来不及穿衣服就往外跑;有老人和小孩还没反应过来,被倒塌的墙面和屋顶埋在了下面。
跑出来的人们聚在广场上,陈家村微信通知群里,消息不停弹出:谁家房子塌了,谁家的人被压在下面了……村民们相互帮忙,在一堆堆砖块和木头中间,寻找着他们的亲人或是邻居。
救援力量到达时,村内大部分遇难者的尸体已经被抬出来,放在空地上。四社一位村民说,陈家村共有七个社,遇难者有二十余人,其中四社有八人遇难。
婆婆告诉绽玉娟,大家跑出来以后没有地方去,在村里空地上点燃玉米秆,围着坐了一夜。一整晚,绽玉娟和同在厦门的亲友们都盯着网上的直播,讨论着要不要回家。有人说,回去也帮不上忙。“我要回去”,她对丈夫说,“把孩子抱在怀里面,跟他们睡一会儿、玩一会儿也是好的。”
这天,光她知道的,至少有14个在厦门打工的老乡要赶回去。其中,一位和绽玉娟同村的朋友被告知,母亲压在屋子里已经确认遇难,他急匆匆搭上了最早一班飞机。
绽玉娟和另外四个人结伴往回赶,路上,他们讨论着村里的救援情况、可能收到的经济补偿,没有人提起和死亡有关的事。晚上八点多,在从兰州机场到陈家村的路上,绽玉娟收到朋友发来的视频,孩子们和奶奶坐在帐篷里,身上没看到明显的伤痕。
绽玉娟他们五个人赶到陈家村安置点,已经是20日凌晨一点,村民们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歇下。夜里气温降到了零下16度,五个人站在帐篷外围着火炉取暖,因为回来太匆忙,他们的身上都只穿着单衣。绽玉娟急着见孩子们,可电话打不通了。
夜深了,帐篷内慢慢安静下来,只有救援人员还在忙着安置刚回来的人、给没有厚衣服的村民找棉大衣。被安排在一顶帐篷落脚后,绽玉娟盯着一个睡去的女孩看了好一会儿,走到女孩脚边问,“这是?”孩子掀开被角,露出全脸,她有些失望——不是大女儿。
震后的第二晚,她又是一夜没睡。早上七点半,夫妻俩挨个掀开帐篷门帘,叫着孩子们的名字。在同排最里面的一个帐篷,终于有人应声,小儿子见到绽玉娟,抱着她亲个不停。
“不让冬天闲着”
19日零点30分左右,已经睡下的马木海麦接到了堂弟的电话,“你快来”,堂弟语气急促,“两个小孩被压着了,没了”,说完,便匆匆挂掉了电话。
回家路上,马木海麦的脑子一团乱。一个月前,他通过劳务介绍到广州工作,这是近二十年来,他头一次出远门打工。过去,他总念着孩子还小,不想离家太远。如今,四个孩子中,大女儿和二儿子已经成家,最小的老四也已经九岁。他想,该出去赚点钱了。
地震的前一天,他和家里打视频,儿媳说两个弟弟太过调皮,他叮嘱两个孩子,“爸爸走了,你们要把嫂子的话好好听。”视频里,孩子笑着问他什么时候回家,“两到三个月,爸爸就回来了”,他说,那时候春天来了,临夏暖和点,就在家附近打点零工,能多陪陪家人。
19日下午2点多,马木海麦赶到陈家村,看到两个儿子躺在空地上,“没办法,送(下葬)掉吧”。
在这场地震中失去孩子的,还有同村另一位打工者佘满素。他原本计划着,等来年三月回家的时候,从惠州买一辆小自行车,那是19号晚上打视频电话时,他答应女儿的。作出承诺几个小时后,就传来了女儿去世、母亲和老婆受伤的消息。
一年365天,佘满素像候鸟一样,在南北方辗转,哪里有活儿就去哪里。西北的冬天太过寒冷,工地没法开工,为了不让冬天闲着,村里大部分务工者会去到南方城市——那里的厂子一年四季都招人,流水线工作,不需要太高的学历。
夏天,佘满素在新疆的工地上做杂活,十月底,他回到积石山待了十几天,便又和同村的两人结伴去到广东惠州,到一家电视机工厂打工。
他的任务是给电视机配件打上螺丝,每天工作约10小时,时薪是19元,这是经过几手劳务公司“层层抽成”后的价格。佘满素只读到小学一年级,这对他来说算是份不错的待遇,比在工地上搬砖轻松许多。他说,如果文化程度高点,就可以找到时薪30元的岗位。
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佘满素还是无法习惯没有孩子在身边的生活。只要一有休息时间,他就通过视频看看屏幕另一端的老婆孩子,常常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今年,他18岁的儿子第一次出远门,开启了家里又一代人的打工生活。
外出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佘满素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陈家村,无工可打的时段从十一月开始,持续到来年二月底,如果不出去,四个月的收入为零;以厂里每月五千元的工资为例,外出一个冬天,可以多赚两万元。
出于同样的原因,绽玉娟和丈夫在今年九月离家,坐上了去厦门的动车。在这之前,她的丈夫在积石山周边的工地上打零工,一天收入120到180元,疫情的三年间,一个月可能只有十几天有活干。绽玉娟一家7口人,“根本养不活”。
“这里一年四季都这样吗?”刚到厦门时,绽玉娟对这座南方城市充满好奇:冬天路上也能看到花花草草,气候不像西北那样干冷,闲暇时,坐两三站公交就可以到海边,脚踩在沙子上面,软软的。
一天24小时里,她无数次会想起孩子,最放心不下的是三岁的小儿子:“不知道这个时候他有没有哭,有没有闹?”
下班后到公园散步,看到别的父母带着孩子在沙滩上玩,绽玉娟总会心生羡慕,“要是把我的孩子带过来,也在这里玩,应该会很好。”她想起以前的夏天,他们一家人常带着零食到黄河边玩耍,看河里的人游泳。
第一次到海边,绽玉娟给孩子们打视频,女儿却没有想象中的兴奋,反而有些嗔怪,“你们去哪里玩了,都不带我。”这让她心里过意不去,再到景区时,她只敢拍张照片发过去,配上一句:好好学习,等你放寒假了,我带你来这里。
她喜欢厦门的生活,自由、湿润,与之相对的,陈家村则代表了封闭、落后与枯燥,除了回娘家和到亲戚家串门,她几乎很少出村,到了冬天,没事干,也没有钱赚。
“被迫离开”的无奈
一位77岁的低保户说,“如果不是这(地震),没人会知道我们这里有多穷。”他和老伴、孙女住的没抹外立面的水泥砖房,是四年前政府给低保户建的安置房,和村里那些老旧的土房子相比,算是不错的。
积石山县曾是国列省列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是甘肃省23个深度贫困县之一,2019年,全县2989户13546人脱贫,53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15%,实现整县脱贫摘帽目标。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全县630户2821人剩余未脱贫人口全部脱贫,1389户5989人边缘易致贫人口消除返贫致贫风险,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2014年,厦门市海沧区与积石山县建立结对关系,厦门也成了当地外出务工的首选城市之一。记者采访到的村民大部分只有小学文化,他们就职的岗位集中在电子产品加工、健身器材加工、餐饮服务等行业。
找到小儿子的那天早晨,小儿子问绽玉娟,“你还要不要走?”
“我要走。”她说。
“能不能不走?”
“不走,在家里没钱呀。”
大女儿没有说话,站在一边流眼泪。
三个月前,她和丈夫去厦门那天,女儿也是这样哭,小儿子紧紧抱着她,不让她离开。
对于这种“被迫外出”的无奈,在积石山县从事多年劳务中介的马元深有体会。每年8月份开始,来向他咨询招工的人就多起来。他说,大部分找工作的人都更愿意在离家近的地方打工,“哪怕一个月只能赚三千,我们也愿意守着家里。”
近几年,县里为了鼓励大家外出打工,出台了很多务工奖补政策,比如发放交通补助、对稳定务工3个月以上的代表发放3000-10000元的补助。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22年10月底,县里共输转农村富余劳动力8.124万人。2023年以来,县劳务部门对接厦门、济南、中山、南京等30多家省外用工企业,动员有就业意愿的劳动力外出务工。
一位陈家村村民讲述了自己的打工史,13岁那年,他先是去了邻近的青海化隆县,15岁时从西北远赴上海,在电子厂干了14个月,因为是没到法定年龄的“黑工”,总被克扣工资。在近20年的打工生涯后半段,他的落脚点已经远至广东惠州,但他最怀念的还是开始在化隆那段时间:“都是家乡的人,说话、吃饭都是一样的。”
在陈家村四社村长韩志刚的记忆里,打工潮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村民们先是到新疆、青海从事建筑、修路等工作。大约是2018年,村里的青壮年开始去到广东、厦门和南昌等地务工,“以前去的都是男人,后来进电子厂的机会多了,很多女人也去了。”
四社一共有97户家庭,现在将近80%的人都在外地。打工的好处是经济状况终于有了起色,以前家家户户靠种植玉米、养牛羊维持生计,一年挣不到一万块,现在年轻人一个月在厂里就能挣到三四千。
随着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村里整体经济情况得到改善,韩志刚明显感觉到,近两年有钱了,读高中、上大学的孩子变多了。“像村里五六十岁的人,很多都是不识字的”,韩志刚说,自己只读到了小学二年级,如今他的孩子上小学一年至少要花费四五千。
让他犯难的是,村里也离不开年轻人。就像这次地震发生时,很多人家只有老人和孩子,“如果年轻人在,说不定能带着他们一起逃出来。”即使现在,搬运物资、安葬遇难者这些事情,也都需要从外地赶回来的年轻后生们操持。
一个19岁就离家打工、把父母也接去湖北定居的村民,这几天特意开车赶回了陈家村,他说,就是希望能给亲戚邻居帮上些忙。
钱、房子、生计
沿着陈家村的路,随处可见掉落的砖块、瓦片和木头,甚至是被震掉的大铁门。道路两旁的院门被贴上了“可以入住”或是“不得入住”的字样。村里的屋院结构大体类似,三间主屋正对着大门,左右是两间侧屋。
散落在地的砖块里,有不少是空心砖。和绽玉娟一起从厦门赶回来的马文祥说,一块空心砖六毛钱,一块实心红砖则要一块多钱,为了节省成本,一些村民在建房时,会把空心砖和实心砖混着用。
倒塌的房子中,受损最严重的是土房和木头房。一位村民介绍,相较于水泥房,木房子除了成本低,保暖性和透气性也更好,房龄超过十年的房子,多采用砖加木头的结构。近几年新修的房子则以水泥砖房为主。
去年,马文祥夫妻俩用外出打工攒下的钱,在老旧木房旁边主屋的位置上,建起更稳固、牢靠的水泥新房,地基被垫得很高,从院子走上屋里,要踏上四级水泥台阶。在抵御自然灾害时,这样的房子显然更有优势,除了台阶和墙面有裂缝外,看不出太严重的破损。
这三间主屋的建造和装修花了大约18万,夫妻俩努着劲儿攒了一年多,政府可以补贴25000元,款项暂时还没下来。今年九月份,新房完成装修,两人还没有入住,就再次去往厦门打工,“不出去打工坐在家里没钱啊”,他说。
和马文祥夫妻俩一样,外出打工者们的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了盖房和装修上。
21日下午,绽玉娟推开自家院门,离家三个月,她仔细打量着屋子,地板砖裂开了一米多长的缝隙,原本贴墙站的衣柜移了位,离墙有十公分的距离,柜门齐刷刷开着把衣服“吐出来”,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掉落在地上。
家里主屋和侧屋都是三年前重新翻修的,今年刚装修完,总计花了30多万,包括公婆的“赞助”,以及借别人的10多万。夫妻俩计划,边打工边还。心疼损失的同时,绽玉娟又有点庆幸,新修的房子结实,如果是之前的土房子,大概率无法逃脱坍塌的命运,“要是家人没了,挣再多钱也没有用。”
因为不知道怎么开口安慰,绽玉娟一直没敢去同村马海林家里看看。马海林是她婆婆的亲外甥,40多岁,在地震中遇难。
马海林家三间主屋和三间侧屋结构类似,墙面用的自制泥巴和成土砖,木棒和木板作屋顶,再盖上一层瓦片,几乎是当地“最低廉”的房子。主屋是十七八年以前修建的,墙体贴上了瓷砖,侧屋建的更早些。按当地风俗,公婆住进相对较新的主屋,马海林和妻子分别住在两间侧屋。他家日子不宽裕,马海林在乡里工作,妻子在家照顾老人和两个读初中的孩子,一家六口人全指着他五千多元的工资。
地震时,屋顶塌落的木板砸在马海林妻子身上,好在墙面是往屋外的方向坍塌,她扒开木板,从临近屋门的位置爬了出去。主屋损毁不严重,公婆也跑了出来。但马海林住的侧屋外面堆了一排玉米秆,压着墙面向屋内倒塌,砖和木头一起砸了下来。妻子叫了几声他的名字,没有人应。邻居过来一起帮着挖人,半小时后,马海林被抬出来,已经没了呼吸。
震后几天,外界的救援物资一批批送达陈家村安置点,但帐篷仍是紧缺,几家几户合住在一个帐篷里,一顶12平米的蓝色帐篷里,最多同时住着八九个人,想翻个身都困难。
走还是留,成了陈家村打工者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低温天气下,房屋重建工作无法进行,村民们可能要在帐篷或是活动板房中度过这个冬天。
绽玉娟还是决定要走,“在家这样待着,也没有什么事做”,她和老板请了十天假,延期不回,可能会被扣工资。
“这个工一年之内是打不了了”,马文祥夫妻俩商量着,老婆先出去打工,他留在家里。因为担心之后房屋定损、重修一类的事务,家里要留个主事的人。这天马文祥到凌晨三点都没能睡着,他在朋友圈写下:好多熟悉面空(孔)已隔离两世。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青深一度
本文由看新闻网转载发布,仅代表原作者或原平台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立场。 看新闻网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或有适当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