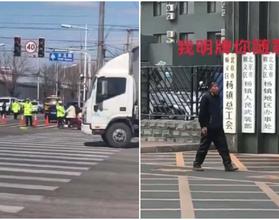前段时间,李海燕又做梦了,梦里有两个人拿着刀要来杀自己。她形容自己像是在幽深黑暗的隧道里独行,偶尔头顶会闪过亮光般的希望,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出口。
一切源于两年前的实名举报。2021年5月,在重庆市某事业单位工作的李海燕,实名举报某市级部门巡视员、纪检组长张玉帆与其妻冉利坐拥26套房产、“吃空饷”八年侵占国家财政资金150万元。她甚至整理出了这26套房产的具体位置。这其中,张玉帆是她领导的领导,冉利是她的同事兼闺蜜。
这一“自杀式“举报在网上引起轰动,李海燕的命运也就此改写。
两年多过去,当初的举报帖已难寻踪迹,舆论已经停息,李海燕却仍然不得安宁——她经历离婚、被恐吓,甚至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门口,被对方打到满头是血。她与被举报者打了四起官司,其中包括三个民事诉讼案件和一个刑事案件。两个民事案件李海燕赢了,但赢得曲折,对方不断上诉,法院多次驳回。刑事案件她也赢了,对方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一年。另有一起民事案件她是被告方,案件正在审理中,她的资产也因此处于冻结状态。

与李海燕几次长谈过后,9月下旬,记者拨通了冉利的电话,想向她了解整个事情的全貌。“她(李海燕)已经疯了,不要理她。”冉利说完,挂断了电话。而在两年前,张玉帆在电话里曾对记者表示,“相信组织的调查,等待调查结果”。
李海燕同样在等待结果。举报后,她几次打电话询问,案件承办人表示,“我们在调查,有新情况会通知你”,李海燕说她至今没有收到过正式的书面回复。被打后漫长的恢复期,她的头发从光溜溜的头皮底下冒出来,半年才缓慢长出四五厘米。短发向各个方向肆意生长,显得有些杂乱,几根白头发突兀地冒出来,仿佛在提醒她已经47岁了——她的娃娃脸,让她看起来总像30多岁。新长出来的头发遮住头顶的伤疤,右眼到鼻梁之间,明显有一道两厘米竖长的凹痕。
领导和下属,金钱与暴力,交织在李海燕的故事里。案子占据了她生活的全部。她喜欢讲案子,一讲起来,嘴里就接连蹦出一个个法律术语,滔滔不绝,圆圆的眼睛始终直视对方。打断她,她很快又会接过话头继续说,好像说得越多,愤怒和委屈就会少一些。
这让她看起来多少有些偏执,但这或许就是举报和反抗的代价——把体制内原本平坦的生活变成了战场。
“朋友”
这是一个曾经的“闺蜜”反目成仇的故事。
李海燕认识冉利十几年了。当时,后者从区县调到李海燕所在的市级单位,大家都听说她丈夫张玉帆是上头的领导。李海燕很快发现,这个领导夫人没架子,她说话好听,做事圆滑,还热情地管李海燕叫“燕子”。再后来,冉利不怎么去办公室上班了,她有时会拜托李海燕帮忙跑腿,隔三差五跟她说自己又去了哪儿玩,还会带些伴手礼。
2014年,冉利带李海燕放贷投资。那几年,民间借贷在重庆以及全国兴起,李海燕很感谢这位姐姐带她一起挣钱。多了经济这层往来,李海燕和冉利从普通同事逐渐变得无话不说,成为闺蜜。李海燕得知,冉利一直在外面以自己或亲戚的名义,做些挣钱的项目。而她也毫无保留地告诉冉利,自己老家的房子快拆迁了。
没过多久,冉利再次邀请李海燕一起借贷给一名冉利的熟人。
这次,李海燕借出了刚收到的几百万拆迁款,其中也包括母亲的那部分。正如上次投资一样,她相信冉利,“细节都是冉利安排,只管签字、打款。”她始终觉得,有领导家属背书的冉利不会乱来,毕竟身份地位在那。
李海燕的父母是做生意起家,她从小到大生活宽裕,没缺过钱。婚后,她和丈夫经济各自独立,办过财产公证。钱怎么花、投资到哪,她习惯自己做决定。她对钱的事情一向爽快,有同事朋友找李海燕借几十万周转,她连抵押都不要。出事后,有朋友开玩笑说,“这事发生在你身上,并不觉得意外。”
她的性格也一向大大咧咧,看不惯的人和事,她总会直说。某种程度上,表现得热情大度的冉利,是李海燕愿意结交的朋友类型。但李海燕丈夫对冉利的印象一直很差。他觉得她说话浮夸且高调,他多次告诫李海燕,不要和冉利这家人走太近,觉得对方属于典型的区县“土皇帝”,眼里只有“关系”和“金钱”,他不与他们往来。
李海燕没把丈夫的话当回事,她觉得“领导总是有底线的吧”。
但这次,李海燕借出去的钱没有收回来——债务人无法偿还后,冉利拒绝债务人提出的以物抵债等还款方式,非要吃对方的利息,并因此与李海燕产生矛盾,有了嫌隙。再后来,冉利甚至强行单独去执行她们共同的债权,否认李海燕的应得份额。
李海燕的生活从财产危机开始,全方位分崩离析。
举报
官司接踵而至。
一开始,是冉利以儿子冉裕林的名义私自向法院申请执行共同的抵押物,李海燕向法院申请案外人执行异议,冉裕林否认她的份额,法院经审理后不支持冉裕林。之后,李海燕向渝北法院起诉冉裕林合同违约,法院判决冉裕林支付李海燕资金。再后来,冉利又以虚假合同纠纷起诉李海燕,李海燕先前借出去的钱还没收回来,反倒欠了上百万元。
同在体制内工作的李海燕丈夫也受到了影响。李海燕记得,从2020年开始,丈夫不断被匿名举报。他工作向来谨小慎微,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相关部门调查后,确认不存在问题。但举报一件接着一件,他不断需要自证清白,影响了升迁和前途。
有一段时期,李海燕经常在丈夫单位帮他准备回复材料——对方举报捏造的事情,他自己都不知道具体情况,只能找李海燕问来龙去脉。某一天,又是忙到深夜,李海燕看着正在翻材料的丈夫,突然觉得很疲惫,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
“我们离婚吧。”她突然开口。
丈夫抬头看她,愣了一下,一边继续埋头整理手里的东西,一边说,到现在这个地步,离婚也没什么用。
丈夫是李海燕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两人大学时就认识了。李海燕一直很佩服丈夫,他成绩好,读书多,工作也比她好,看问题比她更客观更理性。即便这次因为出事后,丈夫也从没和她吵过架。这些此时都加深了她对他的愧疚。她明白,这些没来由的举报缘于自己和冉家的那些纠纷。
那之后,李海燕几次提出离婚。丈夫最终同意了,两人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李海燕知道,即便以后问题解决了,也不可能复婚了——她总觉得自己犯了这么大的错,很愧疚。
李海燕的电脑、打印机、法律书籍,时常陪她到深夜
离婚并没能让李海燕的处境好转起来。2021年,她听说冉利的侄女王鑫到处打听自己13岁女儿的消息。女儿住校,不知道父母离婚,也不知道家里正在发生着什么。
李海燕和前夫紧张起来。一贯理智冷静的前夫第一次对她发了脾气,“你看看你都结交了什么样的人!无法无天了。”李海燕报了警,警方对王鑫进行了警告。
女儿是李海燕最大的软肋也是她的底线。她想着,不能等了,要主动出击,举报对方。
她先找单位领导请了一周的年假。准备材料阶段,她想过很多种可能性——失去工作、被报复、被辱骂。想到晚上焦虑得睡不着,从床上爬起来,挣扎到电脑前,整理要举报的内容。反复听自己和冉利的微信语音、翻文字记录,找出一些可用的材料。
李海燕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的计划,她知道即便是前夫或者母亲,都不会支持她这样的行为,他们会觉得“这样的事情最好私下解决,不要闹到台面上”。她也犹豫过到底要不要举报,但她冥冥之中又觉得,自己必须这样反抗,否则这场战争没有尽头。
于是,她写下了那封改写命运的举报信。
文章发布后,她的电话被打爆了——各级领导都叫她删帖,甚至找她的前夫,还有她走得较近的同事来做工作,找哥嫂来做工作。媒体联系她想要采访。她不敢接陌生电话,也不敢回家,在宾馆躲了一周。
一个深夜,她的手机突然响起,一个陌生来电,接通后是一连串辱骂。她强作镇定,不回复一句话,只是默默录音。她觉得当初都是因为自己粗心大意才落入陷阱,现在她的每一步都不能出错,她得把所有和对方的接触都留作证据,才能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战斗的代价
独自走路的时候,李海燕总会小心翼翼地打量四周环境。白天人少的街道、光线昏暗的地下停车场,都让她神经紧张,她会一边加快步速,一边随时回头看后面是不是有人跟踪。平时如果没人一起,她几乎不愿意出门。
这都是被殴打留下的“后遗症”。
2022年9月,在重庆市高级法院门口,一个比李海燕高出一头的壮实男人,用手机猛砸她的头。她摔倒在地,像拖把一样被男人揪着头发拖到旁边。男人继续猛砸她的头。一旁那个戴着帽子、穿横纹连衣裙的中年女人则夺走了她的手机,三次猛摔在地,又在路边的石柱上猛砸。她用尽全身力气,想要毁坏这个手机。
男人最终被法警拉走。李海燕从拳头、辱骂和尖叫声中站起来,左手捂着头,甚至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只觉得整个头痛得要炸开了。她努力站起来,头发散在眼前,头顶热乎乎的,血从头顶流下。
打她的是冉裕林,而摔她手机的女人,是冉利。
被紧急送到医院后,医生剃掉李海燕头顶流血伤口处的一小块头发,方便止血。剃掉之后发现她头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伤口和淤青,只好剃光她所有的头发。进入麻醉状态的李海燕隐约听说要剃光她的头发,难过极了。她从小到大都是长发,头发最短的时候也及肩。
术后醒来,她发现自己成了光头,脸肿得老高,眼睛只剩一条缝,“像个废人”。但她来不及难过,并很快要求转院——因为害怕对方再找过来报复。
这是她实名举报之后最“惨重”的一次代价。
她还记得2021年5月,举报后刚回去上班那几天,办公室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以前隔着几米远就招呼她“燕儿姐”的热情同事,突然换了副面孔——一句话不说,嘴角勉强牵出一个弧度表示礼貌。
也有一些意料之外的鼓励,有以前不怎么说话的同事在电梯里遇到她,默默竖起一个大拇指。还有一些不认识的网友给她打电话、加微信,让她加油。她去财务科,一位同事问她“接下来怎么办”,表情里透露着对她的担心,眼睛里甚至含着泪光。
面对单位的领导和同事,李海燕有些不自然,怕被人算计,“总觉得他们不愿意站出来支持我,都戴着面具,充满假意,都不值得深交。其实他们都知道冉利吃空饷的事。”
逐渐地,李海燕也把自己封闭、包裹起来。她和以前的朋友都断了联系,生活重心倾斜在案子上。以前性格开朗、和谁都能聊上几句的她,不再和同事交流任何工作以外的话。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处在惊慌失措中。说起自己的经历,眼泪会不断往外溢。用纸巾擦完眼泪,再攥在手里紧紧握成纸团。仿佛离开了这个纸团,她的焦虑就无处安放。
一段时间后,她发在公众号上的举报信消失了。她打电话去问举报调查的后续,案件承办人说,“我们在调查,有新情况会通知你”。她补充了新情况,但没有收到过正式书面回复。
临近崩溃边缘时,她经常要请假去有关部门,也要跟单位领导交流汇报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状态。领导开始有些同情她了,尤其是她去年被打后,单位领导明确让她走司法途径解决问题,办理好请假手续,只是不赞成在网上举报和写出单位名字。
李海燕有时候也觉得孤独。她最好的朋友是大学时的一个女同学。这些烦心事,李海燕经常找她吐槽。就在前年,这位最好的朋友突然被发现胰腺癌晚期,短短一个月就去世了。李海燕甚至没来得及见她最后一面。她忽然觉得,除了生死,很多事或许没那么重要。
纠纷发生前,李海燕一直过着大多数人所羡慕的、一帆风顺的人生。
她在家排行老二。小时候父母在外地做生意,她跟着婆婆(奶奶)长大,性格独立,大小事都自己做决定。1995年到西南政法大学读专科,认识了当时正在读本科的前夫。后来她又凭自己的努力,考上本科。
早些年,她在律师事务所、法院实习,之后又应聘去一家做电梯业务的公司干过销售。结婚后,她和这个城市里的很多女人一样,想要以家庭为重,于是进入新单位工作。上班、带娃、旅行,生活简简单单。接触的朋友基本都是体制内的人。周六日打麻将逛街,年假出去自驾游。
父母对李海燕的教育是,与人为善,为人一定要讲信用,要能吃得亏。母亲曾以李海燕为傲,认为这个女儿见过世面,工作也不错,熟悉投资房产的信息和政策,也因此将手中的闲钱转给李海燕帮忙打理。
出事后,妈妈开始埋怨她。有一段时间,她每天随时随地打电话找李海燕还钱,埋怨她太笨了,不该轻信别人,让家人和她一起沦为笑柄——周围免不了有人说风凉话,“李海燕不晓得把她老妈的钱整到哪里去了”。李海燕和哥哥、妹妹的关系此前一直很好。这次出事后,大家基本没联系了。这几年的春节,李海燕都是一个人过。
对女儿,她也是有愧疚的。从前,女儿的开销基本由她主要负担。三年前,女儿小学毕业,提出想读国际学校。当时李海燕资产被冻结,拿不出钱让女儿读更好的学校。
在女儿面前,她和前夫一直扮演家庭圆满,避免让女儿感受到离婚带来的变化。每个周六日,前夫会回到家里,等待女儿从寄宿的学校回家,一家三口还像以前一样一起吃饭。女儿对此一无所知,只是有时会埋怨说,“妈妈管我变少了。”
等一个结果
最近几个月,李海燕收到的最好消息是一封刑事判决书,殴打她的冉裕林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一年。判决书称,“冉裕林用自己的手机连续、多次砸向李海燕头、面部等身体部位,致使李海燕右侧颞顶部、顶部头皮撕脱伤、眉间皮肤软组织撕脱伤等,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
今年2月,李海燕通过诉讼程序拿到重庆市高级法院门口的监控录像。视频只有一分半钟,她反复在手机上按播放键,强迫自己回忆那些屈辱和伤痛,告诉自己要把官司打到底。她说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初的举报,唯一后悔的是自己当初太天真,太过于信任别人。
经过这几年,她变得坚强了。案子推进过程中,她开始自学法律条款,重新梳理以前和对方的转账记录,经常要跑往市、区两级多个有关部门。有一段时间她为了省钱,不找律师,开庭自己去。
与多方打交道的过程中,她逐渐学会了一些技巧,也学会了用法律条理和逻辑说话。即便在生活中,她脑子里也满是案件的细节、证据、流程,连开车都在想。想到了什么,怕忘记,就边开车边忙着发消息告诉律师,有一次差点出了交通事故,“一开始是想把这些钱扳回来,现在的想法是,一定要有一个结果,要真相。”
她坚信自己会等到一个说法,她不能打败仗。
被打后在家养伤那两个月,几乎每天她都要提醒自己,“不能因为被打,精神就倒下,否则对方就是真的赢了”。她因此坚持健身,强撑着不让自己垮掉。
她与债务人也仍然在正常沟通。当初和冉利借出去的钱,两个冉利当初介绍的债务人都没有赖账,还在正常沟通。李海燕觉得他们也是身不由己——经济形势变了,建筑行业遇到困难,还不上钱,她也没有强行要他们还钱。
和李海燕接触最多的几名律师都能感觉到,她有时显得执拗。为李海燕代理她起诉冉利的妨害作证、虚假诉讼案的黄律师,一度因为案件思路的分歧,跟李海燕发生过争吵。在他看来,她对待案件特别抠细节,有些认死理。
“她懂一些法律,但是对法律的理解又不够,有时会反复揪住一个事实,理解不了为什么现实和法条的不一样。”黄律师说,她想到案件的一些细节就会立刻发语音过来,不管深夜几点。他一早打开手机,经常是她发来的满屏五六十秒的语音条。“她急于表达自己,需要人倾听和分析。觉得自己是对的,就一定要做下去。”
黄律师此前在外地公安局的刑侦大队负责案件预审,做警察做了十多年、经手七千多个案件,遇到过很多被骗钱的案子,也会痛心疾首地骂当事人怎么这么傻。这其中,很多人陷在各种复杂的经济案件中,一直不得脱身,最后索性放弃了。
李海燕不一样,她总是一丝不苟地和律师一起梳理案件的有利和不利证据、补充材料,打印出来有四五百页。案子一度难以推进时,她也会当面追问理由。回家后,再找出对应的法条、证据,给对方发长长的消息。
“现在斗争,不只是为了自己斗争。连我一个体制内的人都这么难,普通老百姓不知道多难。”她说,自己会带着这样的想法去战斗。有人来咨询她,她也会给对方一些建议。
李海燕的战斗还没结束,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
但她觉得,这几年,该做的事她都尽力去做了,也就没那么焦虑了。她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每天早上七点左右起床,健身、吃早饭、上班下班,睡觉前听听播客。最近她听到罗翔讲《理想国》,“正义不是强者的利益,要相信正义,正义是不败之地。”她把这几句话记下来,在微信上发给一位朋友。
前段时间,女儿似乎察觉到了家里的一些不对劲,但看到疲惫且面露难色的妈妈,她懂事地没有多问。她只是催着妈妈和她一起学英语。她想以后出国读书,带着妈妈一起出去。
(全文转自凤凰WEEKLY官方账号)
本文由看新闻网转载发布,仅代表原作者或原平台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立场。 看新闻网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或有适当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