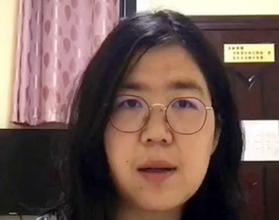这是一篇迟到的文章。张展现在危在旦夕,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她,关注她,声援她。
在武汉疫情之前,我在推上就看到张展在街头举伞抗*争而被X拘的报道,开始关注她,我当时并不知道她是被吊照的律师,金融学硕士,只是为上海这个抗争者不多的大城市有这样一个勇者开始注目于她。
武汉封城当夜,我带着老人们逃到广州郊区隔离避疫。在终日焦虑与痛苦中,一天看到武汉同道群中有人说上海的张展来武汉采访,并问有人是否能接待她?我不假思索的回答道:让她住我家吧,我家房子正好空着。那时武汉正是极度紧张的时刻,我没想到她会深入虎穴。于是,我立马用电报联系了她,告诉了她房子的密码锁号码,并跟她说我家之前接待过很多同道,让她不要拘束。于是张展从火车站下来后第一站就在我家落脚了。
我家之前确实接待过南来北往的很多同道,但都是熟识的,如出来后的文飞、老郭、老唐等,张展却是唯一一个之前没见过面的。当时我岳母得知有人住我家时问我认不认识人家,我说是网友没见过面,岳母有点不高兴,我只得用她听得懂的语言解释:人家是上海的律师,大过年的来武汉当白求恩,这个时候,我们总得做点什么吧。岳母也就没说啥。也许,我当时不假思索的让她住我家时是带着一点愧疚的:在最风声鹤唳的时刻,我逃离了,而张展一个外地人,却来了。
第二天晚上,张展联系我说家里的水管放不出热水,她说她想洗澡,声音非常疲惫。我说走之前还好好的,就让她去试厨房的阀门,鼓捣了半天,原来是水闸自动跳了。我遵守圈内的规则,不问她每天在干嘛,只叮嘱她要多保重。那段时间我开始发起为李文亮造铜像,以及呼吁救助已感染的同学家人的事,实在没精力和她交流什么。
没过几天,张展告诉我说她要换地方住了,说我家离市中心太远,她去火葬场和医院都不方便,骑自行车往返得一整天。我表示理解,说那好。我家位于三环边上几公里处,过去是郊区,出门没车的话确实有点麻烦。我当时每天揪心的关注疫情,没有去想一个女孩子一个人骑着单车在那个大城市是如何辛苦的奔波的。
在广州自动隔离结束后,因为发起造铜像的事,我不断被从化熊猫骚扰传唤。偶尔也去看墙外张展的报道,发现关注者开始并不多,每次她的声音都很疲惫,容颜憔悴,声音沙哑,我佩服她的执着,却也爱莫能助。
四月底,我返回了武汉,知道她还在,我立马联系她,说要请她吃顿饭。我平时很少请人吃饭,因为疫情前就被失业了,生活一直拮据,我是感佩于她的精神,总觉得欠她点什么。那天正好老朋友卫小兵来看我们,于是,我们找了一家汉口的湖北菜馆,张展很快的从武昌赶过来了。
第一次见面,却感觉已经是老朋友样。张展个子很高,是那种南方女孩的高,纤细,瘦弱,圆脸,衣着朴素随意,戴着眼镜,说话细声细气的。那天我们点的都是湖北菜,张展吃得很开心,说这是她来武汉几个月吃得最好的一顿。听着感觉有点心酸,那家餐馆也只是中等偏上而已。我问她平时吃的是什么?住哪儿?她轻描淡写的说都是方便面之类的凑合,临时住在小旅馆。她似乎对于物质生活完全不在意的,她忧心的是她能多做点什么,她承认她有时候很疲惫很茫然。一个大上海的金融学硕士如此脱俗,我有点意外。她是那种极其纯粹的人,她完全活在她自己追求的世界中。我认识很多抗争者,但如她般的纯粹者却很少见。
过了几天,来武汉采访写作的雪村兄想见几个本地的同道,我于是约了几个朋友喝茶,那天张展也赶过来了,她基本没说话,都是在听一个本地的医生朋友讲他在一线抗疫的见闻。结束的时候,我和她并肩而行,谈及武汉解封前后民众的心理变化,张展说:即使我们是最少数的人,也要坚持到底。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被她的话打动,我抬头看了下夜空,那晚的月亮,有些清冷的样子。我赞许的向她点了下头,让她保重,目送着她上了一个朋友的车离去。
又过了几天,雪村兄要离汉,我和朋友们为他饯行。张展也来了,那天,我们吃烧烤,七嘴八舌的聊疫情之类的话题。疫情仿佛要结束了,但张展似乎并没有要结束她的工作的样子。那天不知是谁拍了一张我们吃饭的照片,后来居然落到了武汉熊猫的手中,好在那张照片中的张展只是露出了胳膊和手。
但没过几天,我在一个小群里,看到张展说她被人跟踪了,我开始担心她,因为我知道:武汉的事貌似要结束后,针对她的事可能就要开始了。但我知道无法劝她逃离,以她的执着,她是不会离开她认定的战场的。
很快就传来她被上海警方带走X拘的消息,我听说她是被戴着镣铐押送上的火车。我在群里看到善良热情的本地同道X大姐感叹:我为张展熬好了藕汤,要她来家喝的,可她却被带走了。
张展被抓后,有天夜里我突然饿醒了,爬起来到处找吃的,突然在客厅的角落里发现了一箱娃哈哈八宝粥,上面已经蒙上了灰尘。我从来不爱吃这个,也没有人送过这个来。我想这应是张展留下来的。深夜吃着她留下的食品,感觉很甜,想到她的遭遇,又觉得苦。后来我还发现了一瓶稻花香的酒,我不喝酒,家里也不存酒。我想这也应是她留下的。可她后来几次见面从未提及。张展就是这样是一个毫不世俗的人。我当时的妻子因她被抓郁郁寡欢。我只有安慰说:这几乎是预料之内的事情,从她走下武汉的火车那一刻就开始了。这些年,我们一次次目睹我们的朋友,包括自己,落入敌手,而我们却毫无办法。
跟张展在武汉的三次见面中,我发现她总是在倾听,很少说什么,更没有什么高谈阔论,也许这就是公*民记者的样子。她似乎在我们之中,又仿佛在我们之外。
后来我听到一个张展在武汉的故事:在一次聚会上,一个朋友善意的劝她找个工作,张展反问道:我为什么要找工作?气氛有些尴尬。也许在她看来,在武汉坚持就是她的工作,是她全部的工作。对于一个对物质生活几乎没有欲望的抗*争者来说,世俗上的工作是最没有意义的。
后来我去翻看她的文字,看到她说:“当然应该寻求真理,不计成本地寻求。真理一直是这个世界最昂贵的东西,它就是我们的生命。” 如此的文字,在这个时代,已经很少看到。我和很多朋友也写不出,即使写,也不会如此直接了当,斩钉截铁,这是属于张展独有的气质。重要的是,她不仅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去做的。如她的自述:我不过是想做个好的基督徒。张展就像个没有任何伪饰的孩子,总是毫无保留的发出她的声音,即便声音沙哑,面临险境。
张展被判当天,我为她写了首《神的女儿》的诗表达声援。很多人不太理解她在里面的绝食抗争。在我看来,她的抗争已经升华到了神性的高度,她是属于神的。我们都不希望她做林昭,可她有她自己的道路和生命。一个朋友曾问我:她为什么不上诉?我说:对于一个被吊照的前律师,她完全否认了它们的合法性,她怎么会继续配合那种法庭游戏?我认为,要理解张展,只有从基督徒的角度才能真正进入她的世界。
最近,张妈妈发出了她病入膏肓,走路都要人搀扶的消息。以前对她并不理解的亲哥哥也开始在推上为她发声。这着实让心急如焚,我们担忧她是否会成为另一个晓波。
艾晓明老师最近在文章中说:张展已经是一个拷问,她标记出了我们的处境:理性的失效,生存依赖于道德的模糊含混,平静来自漠视和无动于衷。这种灵与肉的分裂状态,如果你不能改变,只有接受。
今天,张展确实在拷问着我们,也许,会一直拷问下去。
2021/11/3凌晨于宁。
希望有一天能再请她好好吃几顿饭。
附:
《神的女儿——给张展》
像一只笨拙的鹰
你从浑浊的黄浦江畔
飞到更加浑浊的长江之滨
在这个哀哭与悲泣笼罩的城市
你倾听、记录、行走
像那个执拗的孩子
你不断发出尖锐的声音
小区,火车站,火葬场
你穿行在这个恐惧之城
穿过盯梢、冷漠与荒诞
用疲惫而坚韧的声音
掀开谎言层层包裹的衣角
几个月的方便面
廉价的宾馆房间
你的身体日益瘦弱
你的灵魂却一直在攀高
你说:应该有人站出来
自由必须去争取
你推倒阻碍你的栏杆
人们骂你是泼妇
可悲的人们啊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
罪
就像你不知道你的名
神的女儿
你的国不在这里
可你却要像天使一样
来苦地吃苦
到疫地访疫
神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沉沦的世界听不懂
手握权柄的法老听不懂
你绝食的抗争它们更听不懂
神的女儿
没有人可以审判你
你的存在
也是对我们的审判
神说:看啊,那些怯懦的人们
神的女儿
你没有用满嘴的大词去启蒙
你只是像苦行者那样去行走
你的语言简短而平实
哪怕没有多少人倾听
你也坚持不断的诉说
你像不是在对人说
你是在给神交答卷
神的女儿
镣铐和约束带
一直捆缚着你的身体
可你的灵魂永远是自由的
今日,你将被审判
那是罪人的法庭
神的女儿
唯有神
才可以审判
没有人可以审判你
那些审判你的
也必将被审判
本文由看新闻网转载发布,仅代表原作者或原平台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立场。 看新闻网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或有适当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