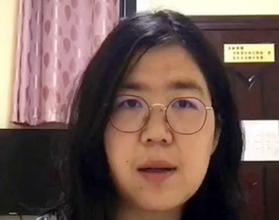這是一篇遲到的文章。張展現在危在旦夕,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她,關注她,聲援她。
在武漢疫情之前,我在推上就看到張展在街頭舉傘抗*爭而被X拘的報道,開始關注她,我當時並不知道她是被吊照的律師,金融學碩士,只是為上海這個抗爭者不多的大城市有這樣一個勇者開始注目於她。
武漢封城當夜,我帶着老人們逃到廣州郊區隔離避疫。在終日焦慮與痛苦中,一天看到武漢同道群中有人說上海的張展來武漢採訪,並問有人是否能接待她?我不假思索的回答道:讓她住我家吧,我家房子正好空着。那時武漢正是極度緊張的時刻,我沒想到她會深入虎穴。於是,我立馬用電報聯繫了她,告訴了她房子的密碼鎖號碼,並跟她說我家之前接待過很多同道,讓她不要拘束。於是張展從火車站下來後第一站就在我家落腳了。
我家之前確實接待過南來北往的很多同道,但都是熟識的,如出來後的文飛、老郭、老唐等,張展卻是唯一一個之前沒見過面的。當時我岳母得知有人住我家時問我認不認識人家,我說是網友沒見過面,岳母有點不高興,我只得用她聽得懂的語言解釋:人家是上海的律師,大過年的來武漢當白求恩,這個時候,我們總得做點什麼吧。岳母也就沒說啥。也許,我當時不假思索的讓她住我家時是帶着一點愧疚的:在最風聲鶴唳的時刻,我逃離了,而張展一個外地人,卻來了。
第二天晚上,張展聯繫我說家裡的水管放不出熱水,她說她想洗澡,聲音非常疲憊。我說走之前還好好的,就讓她去試廚房的閥門,鼓搗了半天,原來是水閘自動跳了。我遵守圈內的規則,不問她每天在幹嘛,只叮囑她要多保重。那段時間我開始發起為李文亮造銅像,以及呼籲救助已感染的同學家人的事,實在沒精力和她交流什麼。
沒過幾天,張展告訴我說她要換地方住了,說我家離市中心太遠,她去火葬場和醫院都不方便,騎自行車往返得一整天。我表示理解,說那好。我家位於三環邊上幾公里處,過去是郊區,出門沒車的話確實有點麻煩。我當時每天揪心的關注疫情,沒有去想一個女孩子一個人騎着單車在那個大城市是如何辛苦的奔波的。
在廣州自動隔離結束後,因為發起造銅像的事,我不斷被從化熊貓騷擾傳喚。偶爾也去看牆外張展的報道,發現關注者開始並不多,每次她的聲音都很疲憊,容顏憔悴,聲音沙啞,我佩服她的執着,卻也愛莫能助。
四月底,我返回了武漢,知道她還在,我立馬聯繫她,說要請她吃頓飯。我平時很少請人吃飯,因為疫情前就被失業了,生活一直拮据,我是感佩於她的精神,總覺得欠她點什麼。那天正好老朋友衛小兵來看我們,於是,我們找了一家漢口的湖北菜館,張展很快的從武昌趕過來了。
第一次見面,卻感覺已經是老朋友樣。張展個子很高,是那種南方女孩的高,纖細,瘦弱,圓臉,衣着樸素隨意,戴着眼鏡,說話細聲細氣的。那天我們點的都是湖北菜,張展吃得很開心,說這是她來武漢幾個月吃得最好的一頓。聽着感覺有點心酸,那家餐館也只是中等偏上而已。我問她平時吃的是什麼?住哪兒?她輕描淡寫的說都是方便麵之類的湊合,臨時住在小旅館。她似乎對於物質生活完全不在意的,她憂心的是她能多做點什麼,她承認她有時候很疲憊很茫然。一個大上海的金融學碩士如此脫俗,我有點意外。她是那種極其純粹的人,她完全活在她自己追求的世界中。我認識很多抗爭者,但如她般的純粹者卻很少見。
過了幾天,來武漢採訪寫作的雪村兄想見幾個本地的同道,我於是約了幾個朋友喝茶,那天張展也趕過來了,她基本沒說話,都是在聽一個本地的醫生朋友講他在一線抗疫的見聞。結束的時候,我和她並肩而行,談及武漢解封前後民眾的心理變化,張展說:即使我們是最少數的人,也要堅持到底。我心裡咯噔了一下,被她的話打動,我抬頭看了下夜空,那晚的月亮,有些清冷的樣子。我讚許的向她點了下頭,讓她保重,目送着她上了一個朋友的車離去。
又過了幾天,雪村兄要離漢,我和朋友們為他餞行。張展也來了,那天,我們吃燒烤,七嘴八舌的聊疫情之類的話題。疫情仿佛要結束了,但張展似乎並沒有要結束她的工作的樣子。那天不知是誰拍了一張我們吃飯的照片,後來居然落到了武漢熊貓的手中,好在那張照片中的張展只是露出了胳膊和手。
但沒過幾天,我在一個小群里,看到張展說她被人跟蹤了,我開始擔心她,因為我知道:武漢的事貌似要結束後,針對她的事可能就要開始了。但我知道無法勸她逃離,以她的執着,她是不會離開她認定的戰場的。
很快就傳來她被上海警方帶走X拘的消息,我聽說她是被戴着鐐銬押送上的火車。我在群里看到善良熱情的本地同道X大姐感嘆:我為張展熬好了藕湯,要她來家喝的,可她卻被帶走了。
張展被抓後,有天夜裡我突然餓醒了,爬起來到處找吃的,突然在客廳的角落裡發現了一箱娃哈哈八寶粥,上面已經蒙上了灰塵。我從來不愛吃這個,也沒有人送過這個來。我想這應是張展留下來的。深夜吃着她留下的食品,感覺很甜,想到她的遭遇,又覺得苦。後來我還發現了一瓶稻花香的酒,我不喝酒,家裡也不存酒。我想這也應是她留下的。可她後來幾次見面從未提及。張展就是這樣是一個毫不世俗的人。我當時的妻子因她被抓鬱鬱寡歡。我只有安慰說:這幾乎是預料之內的事情,從她走下武漢的火車那一刻就開始了。這些年,我們一次次目睹我們的朋友,包括自己,落入敵手,而我們卻毫無辦法。
跟張展在武漢的三次見面中,我發現她總是在傾聽,很少說什麼,更沒有什麼高談闊論,也許這就是公*民記者的樣子。她似乎在我們之中,又仿佛在我們之外。
後來我聽到一個張展在武漢的故事:在一次聚會上,一個朋友善意的勸她找個工作,張展反問道:我為什麼要找工作?氣氛有些尷尬。也許在她看來,在武漢堅持就是她的工作,是她全部的工作。對於一個對物質生活幾乎沒有欲望的抗*爭者來說,世俗上的工作是最沒有意義的。
後來我去翻看她的文字,看到她說:「當然應該尋求真理,不計成本地尋求。真理一直是這個世界最昂貴的東西,它就是我們的生命。」 如此的文字,在這個時代,已經很少看到。我和很多朋友也寫不出,即使寫,也不會如此直接了當,斬釘截鐵,這是屬於張展獨有的氣質。重要的是,她不僅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去做的。如她的自述:我不過是想做個好的基督徒。張展就像個沒有任何偽飾的孩子,總是毫無保留的發出她的聲音,即便聲音沙啞,面臨險境。
張展被判當天,我為她寫了首《神的女兒》的詩表達聲援。很多人不太理解她在裡面的絕食抗爭。在我看來,她的抗爭已經升華到了神性的高度,她是屬於神的。我們都不希望她做林昭,可她有她自己的道路和生命。一個朋友曾問我:她為什麼不上訴?我說:對於一個被吊照的前律師,她完全否認了它們的合法性,她怎麼會繼續配合那種法庭遊戲?我認為,要理解張展,只有從基督徒的角度才能真正進入她的世界。
最近,張媽媽發出了她病入膏肓,走路都要人攙扶的消息。以前對她並不理解的親哥哥也開始在推上為她發聲。這着實讓心急如焚,我們擔憂她是否會成為另一個曉波。
艾曉明老師最近在文章中說:張展已經是一個拷問,她標記出了我們的處境:理性的失效,生存依賴於道德的模糊含混,平靜來自漠視和無動於衷。這種靈與肉的分裂狀態,如果你不能改變,只有接受。
今天,張展確實在拷問着我們,也許,會一直拷問下去。
2021/11/3凌晨於寧。
希望有一天能再請她好好吃幾頓飯。
附:
《神的女兒——給張展》
像一隻笨拙的鷹
你從渾濁的黃浦江畔
飛到更加渾濁的長江之濱
在這個哀哭與悲泣籠罩的城市
你傾聽、記錄、行走
像那個執拗的孩子
你不斷發出尖銳的聲音
小區,火車站,火葬場
你穿行在這個恐懼之城
穿過盯梢、冷漠與荒誕
用疲憊而堅韌的聲音
掀開謊言層層包裹的衣角
幾個月的方便麵
廉價的賓館房間
你的身體日益瘦弱
你的靈魂卻一直在攀高
你說:應該有人站出來
自由必須去爭取
你推倒阻礙你的欄杆
人們罵你是潑婦
可悲的人們啊
他們不知道他們的
罪
就像你不知道你的名
神的女兒
你的國不在這裡
可你卻要像天使一樣
來苦地吃苦
到疫地訪疫
神說: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沉淪的世界聽不懂
手握權柄的法老聽不懂
你絕食的抗爭它們更聽不懂
神的女兒
沒有人可以審判你
你的存在
也是對我們的審判
神說:看啊,那些怯懦的人們
神的女兒
你沒有用滿嘴的大詞去啟蒙
你只是像苦行者那樣去行走
你的語言簡短而平實
哪怕沒有多少人傾聽
你也堅持不斷的訴說
你像不是在對人說
你是在給神交答卷
神的女兒
鐐銬和約束帶
一直捆縛着你的身體
可你的靈魂永遠是自由的
今日,你將被審判
那是罪人的法庭
神的女兒
唯有神
才可以審判
沒有人可以審判你
那些審判你的
也必將被審判
本文由看新聞網轉載發布,僅代表原作者或原平台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立場。 看新聞網僅提供信息發布平台,文章或有適當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