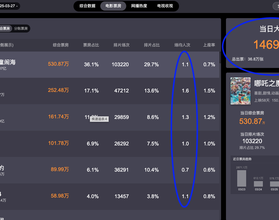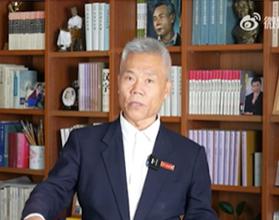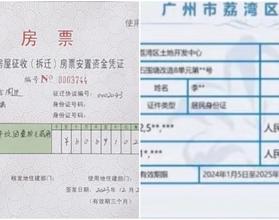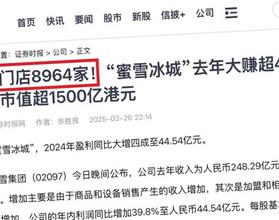隨着《哪咤2》的熱映,哪咤這一形象已經成了民族主義的新象徵。談到這一點時,有朋友忽然問:「印度的戰狼會不會因此罵中國是『偷國』?」
還真是。雖然我沒看到是不是有印度人這麼罵,但可想而知,如果一個源出中國的神靈、人物,被韓國、日本塑造成他們自己的文化英雄,那大概率逃不過我們這邊的罵聲。
反過來,哪咤這個從印度輸入的神靈,現在卻明白無誤被看作是「我們」的,甚至連他的異域出身都不能提。我因為提了一嘴其形象的起源,就有人追着來罵——他倒也不是不知道,但他厲聲質問:「你這時候提哪咤源於印度,是什麼意思?居心何在?」

這種心態當然也可以理解:當一件事物已經被視為「中國」的一部分時,那就應該徹底屬於中國,提及它的異域起源,哪怕你自認只是陳述一個事實,但對有些人來說,就是質疑民族文化象徵,民族自尊心難免被刺痛。
當然,要是較真說,那這部已成為「文化自信」標誌的電影,也大量借鑑了歐美日的動畫拍攝手法(這一點導演餃子毫不掩飾),其製作水平也極大地得益於國內動畫公司承接海外外包業務的長期積累。更不必說,電影這種藝術形式本身就源於西方。
也就是說,不僅哪咤這一神靈形象本身,連背後的藝術創作和表現形式,都意味着「舶來品」已變為「我們」的了。
這樣的景象,當然也不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魯迅說過,中國有必要以開放的態度採取「拿來主義」,積極吸收外來文化。歷史學家羅志田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發現——19世紀的「西潮」到了20世紀就被當作「我們自己的傳統」了:
新文化運動時西向知識分子攻擊傳統時常常提到的鴉片和人力車便是西人帶來的,舶來品竟然成了中國傳統的負面象徵,便最能體現西潮已成「中國」之一部。……西向知識分子把舶來品當作自己的傳統來批判,其實也是受西人的影響。
雖然中國民間近年來諷刺韓國是「偷國」,將「我們」的文化傳統據為己有,但像這樣的「文化調適」(culture appropriation,有時也譯作「文化盜用」)實際上是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極為普遍的情形。

有些外來事物,因為引入太久或完全融入了本國文化傳統,人們已經忘記了它的異域出身——哪咤無疑就是這樣。當然,別提還有無數與佛教相關的形象、概念、詞彙,那都已經與中國文化血肉不可分離了。
有時,事物本身雖然是外來的,但衍生出來的文化卻完全是本土的,例如茉莉花原產印度,極有可能是唐宋時期的阿拉伯商人傳入的,連其名字「茉莉」都是音譯的外來詞,但河北民歌《茉莉花》經常作為中國民族音樂代表傳唱,這一歌曲本身確實是本土文化創造無疑。
在西南山地民族中,人們經常忘記玉米是明末之後才從美洲傳入的植物,而把它說成是當地自古以來就有的東西,有時竟然出現在創世神話當中,一些鄂西人相信玉米是祖祖輩輩都吃的糧食,甚至將之用作山地人與平原人區分的象徵符號。
一百年多年前,俄國學者史祿國(S.M. Shirokogoroff)發現,在清亡之後,東北的一些滿族人實際上已被漢化,但又宣洩着民族主義情緒,其結果:
他們從這一情緒化的立場考慮一切事實,他們的所有觀點都塗上了這種惱怒的自戀色彩。而現在,他們的觀念出現了一種奇怪的混亂和替換。一些純粹是漢族式的制度,他們現在認為是他們本民族的,而一些滿族的制度和風俗,他們卻歸於漢族。例如,辛亥革命一爆發,愛輝地區的滿族人就立即剪掉了他們的長辮子。他們義正詞嚴地說,這是「漢人的習慣」。但是,與此同時,他們確信儒家思想這類中國精神純粹是滿族先民的思想。
這種「文化盜用」在意的不是去考證、計較文化元素的真實起源,而是選取一部分文化材料,用以表徵自己當下的身份認同。納西族的「洞經古樂」原本其實是道教音樂,但如今在外界看來已成為納西族的文化象徵,一如人類學者海力波所言,「納西族精英對本民族文化傳統的改造和重新解釋雖然是在官方話語的引導下進行的,但改造成果卻被用來對納西族『族性』加以本土表述。」

在民族國家出現之前,文化的跨邊界流動是常態,因為文化傳播沒有理由遵從政治邊界的限制。西敏司(Sidney Mintz)簡明了闡明了這一原則:
在任何一種文化中,這些吸納的過程同時也是「據為己有」的過程——按照一個文化自身的方式,把對這個文化而言新奇和不尋常的事物變成它內在的一部分。
哪怕明知是源於異文化的事物,也不妨礙人們這麼認為。《伏爾泰的椰子:歐洲的英國文化熱》一書就揶揄,德國人將施萊格爾譯莎士比亞著作視為一種創作和新的思想深度,「對有些德國人來說,他們認為這表明了德語的優越性。他們聲稱莎士比亞的天才在德國被重新發現,他本應該是德國人,其實他就是德國人。」
同樣地,馬來人、西班牙人、美國人留下的遺產,對菲律賓人來說,就是他們獨特文化認同的組成部分。實際上,隨着現代化的傳播,原本曾完全是歐洲的事物早已不再僅僅屬於西方,「越來越多的例子證明,非歐美地區比北美和歐洲的生活的某些方面更加『西方』。」(《印跡1:西方的幽靈與翻譯的政治》)
這種普世性,當然會被看作是一種文化霸權的體現,然而最為奇怪的是,當中國文化被其他國家吸收時,很多國人又並不為之欣喜,而是覺得「我們的東西被偷走了」。
那種對「偷國」的譴責,表面上看,是對「他們將我們文化傳統據為己有」的反應,但更深一層來看,是因為近代以來中國人從「天下觀」退縮為「國家觀」。「天下觀」意味着,中國文化本身是普世性的,所以日韓越用漢字、學習中華禮儀,那時的中國人並不覺得它們偷,相反,那正證明王道無遠弗屆,「遠悅近來」,那當然是好事。

弔詭的是,這種捍衛文化遺產的衝動,本身卻也是源於西方的政治觀念,因為那是現代民族國家確定無疑的產物。
如果按「偷國」的邏輯,那麼對希臘人來說,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是「偷國」,因為他們都不同程度借用了古希臘的文化遺產,現代希臘國家試圖獨占這一文化遺產,反而激起了爭議:
文化遺產是向所有人群開放的寶庫,而不是一個獨占物,不能否認任何人接觸它們的權利。憑藉作為創造這些文化先輩的後裔身份,要求獨占這一文化遺產,與歷史文化成就屬於全人類的基本原則相矛盾。即使把它提升到正統以及安全的原則,也難以接受這種獨占要求。這樣的宣言即使得到有效的、連續的保護,也只能最後導致民族文化和身份更加糟糕,並迫使國家一直在文化事務上採取敵意姿態。(《希臘的現代進程——1821年至今》
之所以有必要強調這一點,還因為一個原因:如果文化遺產是某一國家或群體獨有的,那它是否有權將之毀壞?塔利班炸毀巴米揚引發激烈爭議,但它作為統治者也在宣示所有權——所有權的意思就是可以隨心所欲地處置自己所擁有的財產。
我能理解一些國人捍衛文化傳統的熱情(有時想想,這總比以前毫不珍惜好),當然,如果能以開放的態度來對待跨文化交流就更好了,但問題是,現實中人們未必保持邏輯一致,倒是會出現一種縫合怪:「我的是我的,你的還是我的。並且我都是對的。」
這,我就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無聲無光
本文由看新聞網轉載發布,僅代表原作者或原平台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立場。 看新聞網僅提供信息發布平台,文章或有適當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