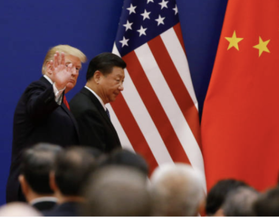文/清簫
今天開始講桐城派和《古文辭類纂》。在學習古文方面,桐城派已構建一個完備的教學體系,各位沿著他們的路走,同時結合自身需求,相信也能學得不錯。
(清)姚鼐《古文辭類纂》
《古文辭類纂》成書於乾隆四十四年,以文體為經,以時間為緯,橫向為讀者展現簡明嚴謹的古文分類,縱向依時代順序選錄各文體的佳作,上溯先秦,中取唐宋,下迄明清,匯集兩千年間七百餘篇文章。此書亦包含姚鼐的評語,闡釋各文體,並指導寫作方法。
上期講《昭明文選》將文分為37類,而《古文辭類纂》借鑑前人之得失,將文分為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讚、辭賦、哀祭13類,在古文文體分類方面更臻完美。深入學古文之前,先要分辨文體,清末民初文史學家姚永朴在《文學研究法》中說:「欲學文章,必先辨門類。」不同文體的性質、功能、作法不同,好比寫議論文不能寫得像記事文。此前介紹的《文心雕龍》、《昭明文選》都重視文章的分類;《古文辭類纂》的編選者姚鼐也深刻明白辨體的重要性,所以此書對古文的分類很嚴謹,各位可以看到,他在大分類中還分上下兩編。

在深入《古文辭類纂》前,我先解釋幾個大家可能困惑的問題:(1)詩算是文嗎?(2)什麼樣的文屬於古文?(3)什麼是桐城派?
此前各位已看到,《昭明文選》選錄的作品有散文,也有詩,有韻之文占很大比重。而《古文辭類纂》不錄詩,以散文為主,有韻之文占比不大。從《昭明文選》的時代(南梁)到《古文辭類纂》的時代(清朝乾隆年間),文學觀念發生了很多變化。
在魏晉南北朝,詩還在文的範疇內,那時主要有「文」和「筆」的分別,《文心雕龍》謂「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有韻的叫作「文」,比如賦、詩、銘、箴,偏重於抒情;無韻的叫作「筆」,比如散文,偏重於應用。中國古代的散文源於《尚書》,韻文源自《詩經》,自先秦時代,應用文和學術著作主要都由散文寫成,如《春秋》、《左傳》、《論語》、《墨子》等經史百家多數是散文。這裡所說的散文不同於現代散文,而是和韻文、駢文相對的,奇句單行,不必押韻且不重排偶。
六朝是駢文興盛的時代,追求整齊的藝術美。但凡事物極必反,文學也是如此,駢文寫到極端處容易華而不實。後來,自唐代韓愈始,散文復興,對抗駢文。韓愈稱散文為「古文」,大家熟知的「古文運動」就是由韓愈、柳宗元掀起的。清代文學家袁枚說:「唐以前無古文之名,自韓、柳諸公出,懼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是古文者,別今文而言之也。」韓愈想要復興的古文即上承先秦兩漢散文形式與文風的那種文;與古文有別的今文指的是駢文,亦稱時文。韓愈另有一大貢獻,即將散文在純文學中的地位進一步提高。本來韻文、駢體比散體更貼近純文學,散體比韻文、駢體更適合於應用文,而韓愈擴大了散文的使用,可謂打開了新的大門。

到宋代,散文成為正宗,古文大盛,詩和文的分別自此越來越明顯。宋人陳師道《後山詩話》云:「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認為像作文那樣作詩便會失去詩的本色,可見詩和文的分界已清晰化。此時,文的涵義已不同於《文心雕龍》所謂的文,昔日的筆已被歸入文中,而詩則從文中分離而出。
雖然詩和文分開了,但賦、箴、銘等韻文文體依然留在文的範疇中。本來韻文和古文是有別的,但因自唐宋以後,文人常以古文寫法作這些韻文,所以將其歸類為古文。在清代,古文包含箴銘、頌讚、辭賦,《古文觀止》和《古文辭類纂》選錄的作品就有韻文文體。
此外,我也想澄清一點,古文不等於八股文,望讀者不要誤會。
有了以上基礎,我們接下來介紹桐城派。
桐城三祖
桐城派是清代古文運動中的正宗流派,代表人物是「桐城三祖」。《古文辭類纂》的編選者姚鼐就是「桐城三祖」之一,三祖依序為方苞、劉大櫆、姚鼐。桐城派的散文理論始於方苞,姚鼐則是光大桐城派的集大成者。
我們先講方苞。方苞,字靈皋,晚號望溪。其才學得康熙帝賞識,曾入直南書房。不久後,方苞入蒙養齋,負責編校御製樂律、算法諸書。康熙六十一年,方苞擔任武英殿修書總裁。《清史稿》記載:「苞為學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禮,篤於倫紀。」「其為文,自唐、宋諸大家上通太史公書,務以扶道教、裨風化為任。尤嚴於義法,為古文正宗,號『桐城派』。」

桐城派對古文寫作的要求很嚴。方苞強調「義法」,主張作文要「雅潔」,認為「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下面逐一解釋。
方苞所謂「義法」一詞,出自《史記》,原文為:「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義法」一詞應拆開解讀,「義」即「王道備,人事浹」,《春秋》微言大義,一字褒貶,引導人行仁義的王道,對人事闡述周全;「法」即「約其辭文,去其煩重」,著史要有法度,精簡文字。當用於文學時,「義」指《易經》所謂「言有物」,不寫空泛或無益的話;「法」指「言有序」,寫作應有條理規範,包含字法、句法、章法。方苞主張的「言有物」也指文以載道,合乎聖賢之道。他主張義決定法,「夫法之變,蓋其義有不得不然者。」

方苞提倡的「雅潔」,字面上看起來很簡單,其實是有具體所指的。什麼樣的例子屬於不雅潔?語錄的口語、魏晉六朝的華麗駢語、漢賦中為求華麗而堆砌辭藻的寫法、詩歌中的雋語、《南北史》的佻巧語,這些都不適合在寫作古文時使用。
劉大櫆是方苞的弟子,他進一步發展了桐城派的文學理論,提出「神氣、音節、字句」說。
劉大櫆《論文偶記》曰:「行文之道,神為主,氣輔之。曹子桓、蘇子由論文,以氣為主,是矣。然氣隨神轉,神渾則氣灝,神遠則氣逸,神偉則氣高,神變則氣奇,神深則氣靜,故神為氣之主。」之前我講過曹丕《典論·論文》,曹丕說「文以氣為主」,而劉大櫆認為作文應以神為主,氣是輔助,作者的精神、感情主導文章的氣。
神、氣都是抽象的,所以需要以具體的音節表現出來。《論文偶記》說:「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蓋音節者,神氣之跡也;字句者,音節之矩也。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准,以字句准之。音節高則神氣必高,音節下則神氣必下,故音節為神氣之跡。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為音節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中國古典文學有很強的音樂性,這一點學詩詞就能感受到,其實古文也講究聲音之美,只是不像近體詩和詞那樣有固定的平仄要求。寫散文是很自由的,但也需注意節奏和音調,文章的節奏可透過句的長短改變,音調高低可透過字的平仄變化,緩急、抑揚、頓挫便從這些細節表現,進而將情感傳遞給讀者。

關於句子長短帶動節奏緩急,我曾在第四期舉了蘇軾〈後赤壁賦〉的例子,「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大家可以回顧,茲不贅述。而關於平仄變化,試看王安石〈讀孟嘗君傳〉文中的例子:「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大家不妨按這樣的節奏念出聲:「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豈足|以言|得士?」平仄交替非常明顯。順便解釋,「足」字我們現在念第二聲,但它曾經是入聲字,是仄聲。
以上介紹了方苞的「義法」以及劉大櫆的「神氣、音節、字句」。在他們的基礎上,姚鼐形成「神、理、氣、味、格、律、聲、色」之說,並主張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並重。
姚鼐,字姬傳,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後任山東、湖南鄉試考官,四庫館纂修官。《清史稿》稱:「鼐工為古文。康熙間,侍郎方苞名重一時,同邑劉大櫆繼之。鼐世父范與大櫆善,鼐本所聞於家庭師友間者,益以自得,所為文高簡深古,尤近歐陽修、曾鞏。其論文根極於道德,而探原於經訓。至其淺深之際,有古人所未嘗言。鼐獨抉其微,發其蘊,論者以為辭邁於方,理深於劉。」姚鼐可謂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桐城派能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主要歸功於姚鼐。
劉大櫆說:「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准,以字句准之。」姚鼐也講文之精、粗處,但有些許不同。他於《古文辭類纂》序目中說:「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
神、理、氣、味是文章最重要之處,偏重於內在;格、律、聲、色次之,偏重於技巧。學古文時,起初感受到的都是文章的粗處(格、律、聲、色),而若想真正學好古文,一定要掌握其精處(神、理、氣、味)。如果只學到格、律、聲、色,那就永遠只是模仿古人。高手的層次是什麼樣的?不留痕跡。姚鼐舉例說:「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云、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效法古文最好的是韓愈,打個比方,他好似將古文融化了,捨棄了原先表面的部份,然後變古人之法為己所用,使人尋不到痕跡,可謂「得魚忘筌」。
下面詳解神、理、氣、味、格、律、聲、色。

神
我們常在文學作品和評論中看到「神」字,可以指作者的精神,或作品的神韻、高妙境界。杜甫詩云:「文章有神交有道」,主人文章寫得有神,賓客也都是英豪,作品的神與作者現實中的為人可以相互印證。姚永朴《文學研究法》說:「古人精神興會之到,往往意在筆先。」我們看周公作的〈無逸〉,文中七段都以「嗚呼」開頭,作者在下筆之前,想必心中已有過無數次感慨與深思,成文只是水到渠成之事,這便是意在筆先。必先有神,然後才可以有文。
理
姚鼐在「神」後補充了一個「理」字。理是貫穿全文的主旨,源自神。姚鼐〈答魯賓之書〉云:「夫內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情當,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厭,猶之其寡矣。……邃以通者,義理也。」胸有成竹,自然能表達出理;若理得當,文章其餘部份自然得當。姚鼐所謂「理」與方苞所謂「義法」之「義」相近。
氣
中國古人無論作詩還是作文,都特別重視氣。有沒有什麼不抽象的物體能形容文章的氣是什麼呢?韓愈〈答李翊書〉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他把氣比作水,將言比作水上的浮物,如果水勢大,則大小物體都能浮起來,古文的氣就像這種水勢。劉大櫆說:「古人行文至不可阻處,便是他氣盛。非獨一篇為然,即一句有之。古人下一語,如山崩,如峽流,覺攔當不住,其妙只是個直的。」先秦與西漢文章大多有此種氣,如李斯〈諫逐客書〉、司馬遷《史記》等。
這種氣不是勉強學來的,所以古人重視養氣。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說:「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盪,頗有奇氣。」有時行萬里路如讀萬卷書,去過哪裡,和誰交友,都會影響一個人的氣,當下筆時卻未必知道氣從哪來。姚鼐〈與陳碩士書〉有句建議:「欲得筆勢痛快,一在力學古人,一在涵養胸趣。」讀書和養氣缺一不可。姚鼐〈答翁學士書〉又說:「無氣,則積字焉而已。」作文若沒有氣,就只是把字堆積起來而已。可見氣多麼重要。

味
氣之後便是味。文章的味可指餘味,即陸機〈文賦〉所謂「闕大羹之遺味」的「遺味」,似言有盡而意無窮。《文心雕龍》〈隱秀第四十〉說:「深文隱蔚,餘味曲包。」文字深厚,有言外之意,即「隱以復意為工」,含蓄曲折,餘味無窮。〈物色第四十六〉所謂「物色盡而情有餘」,也近似這種味。作家若想使文章有味,需積理,多閱事,體悟的道理多了,深度也會漸漸增加。我們學古文時,也應留意感受其味,嘗試放慢閱讀的速度,如姚鼐所言:「緩讀以求其神味。」
格、律
什麼是格呢?格有「法則」的意思。《禮記》有句話:「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漢代經學家鄭玄注曰:「格,舊法也。」律也有「法」的意思,可參考《爾雅·釋詁》。格和律的不同在於,格是告訴人們應該怎樣做,律是告訴人們不該怎樣做,姚永朴《文學研究法》謂「格者導之如此,律者戒之不得如彼」。
古文的格、律是什麼呢?格可以指文章的體裁,不同文體有不同的格,如寫奏議和寫銘誄是不一樣的。格也可以指文章的結構,在寫作前要先謀篇布局,搭建框架。姚鼐〈與陳碩士書〉說:「命意、立格、行氣、遣詞,理充於中,聲振於外,數者一有不足則文病矣。」寫作時,命意之後需立格,格依據意而立,提綱挈領,取捨得當,言之有序,然後再思考文章的細節。《文心雕龍》〈附會第四十三〉說:「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首尾周密,表里一體」;「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也是立格。此外也應知曉文章的律,什麼不該寫,例如方苞所言:「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

聲、色
姚鼐〈與石甫侄孫〉云:「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聲色之間,舍此便無可窺尋矣。」在神、理、氣、味、格、律下了很多功夫,最終全要表現於字句聲色上。文字的聲和色,對作者而言,是最末端的;但對讀者而言,卻是最直觀的,因為它們直接觸及讀者的耳目。如果作者靈感泉涌,感情濃厚,心中構想千萬句話,卻無法精確有力地透過字句聲色傳遞給讀者,豈不是徒勞?所以《古文辭類纂》序目說:「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
前文講劉大櫆時已提及聲的重要性,現在我再多舉幾個例子。詩有一字之師,其實古文也有,稍改一字,聲不同,氣、味亦不同。范仲淹有一篇〈嚴先生祠堂記〉,結尾寫道:「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其實他最初寫的並非「先生之風」,而是「先生之德」。據《容齋隨筆》記載,范仲淹將此文給李泰伯看,李泰伯大為讚賞,隨後委婉建議把「德」字改為「風」字。字的內涵承接上句是原因之一,還有一方面是音韻,「德」是入聲字,發音短促,不如「風」字穩重瀏亮。讚美德行與高風亮節,用平聲字更合適。
字聲、字義是文章的外在,情、氣是文章的內在,應做到內外契合,聲調和情意一致。我們看《古文辭類纂》選錄的〈送董邵南序〉,第一句就是經典範例: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
此文是韓愈為朋友董邵南作的一篇贈序。董邵南懷才不遇,準備前往河北投靠藩鎮,這在韓愈看來,相當於摯友即將投奔叛賊。韓愈既反對董邵南的選擇,也同情他的遭遇,感情複雜。文中看似表達預賀,名為送行,實際上是規勸朋友留步,寫得深婉曲折。首句「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明說古時人稱河北多慷慨悲歌的豪傑之士,想必會珍惜懷才不遇之士,實則暗示現在河北或許不同於昔日,為朋友感到擔憂,希望他三思。
了解韓愈當時複雜含蓄的情感後,我們再讀「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感受其聲調,何其沉鬱曲折!
漢字聲調與情感緊密相關。如上聲舒徐和軟,腔調低而曲折,適合表達沉鬱迴轉之情;去聲激厲勁遠,腔調由高至低,適合表達淒涼之情;而陽平聲適合表達得意之情。各位看此句,選字何其用心!全句沒有一個陽平聲字,連用陰平聲字,且陰平聲字緊挨上聲字,文氣低回沉重,仿佛在徘徊。並使用去聲字「慨」調節,使情感激越,不至於單調乏味。據傳,姚鼐每誦讀此句時,都要數次換氣。大家也不妨試一試,此句真的不適合快讀。

古人學文,主張讀出聲,很有道理,如果走馬觀花般默讀,便少了聽覺上的體會。如姚鼐言:「大抵學古文者,必要放聲疾讀,又緩讀,衹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終身作外行也。」有種方法叫作「因聲求氣」,指的就是透過誦讀感受文章的音韻,進而感悟文章的氣和情。
下面我們來看什麼是文章的色。色可指文采,具體表現很多。姚永朴《文學研究法》稱:「色也者,所以助文之光采,而與聲相輔而行者也。其要有三:一曰鍊字,二曰造句,三曰隸事。」色和聲相輔,字法、句法、用典都在色的範疇內。
修辭手法也屬於色,如比喻、排比、用典等,能使文章不顯枯燥。以李斯〈諫逐客書〉為例,他向秦王嬴政闡述逐客令的危害,以異國珠玉、美女、音樂喻客卿,發人深省,論證有力,辭采斐然,是古文中色佳的範文之一。辭藻是否華麗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內容是否恰當、豐富,以及能否與神、理、氣、味融合。〈諫逐客書〉有一妙處便在於增加層次,使文氣深厚而不靡弱,有大江東流之勢。
他寫道:「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此時論據已足,但李斯作一轉折,假設寶物必須是秦國生產的才能用,將有何後果,隨後舉例滔滔不絕:「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至此,李斯又添一層,再作假設,使氣更加雄厚:「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文采美,意不單,氣不孤。

姚鼐論文采,以方苞「雅潔」為基礎,重視文辭之雅,且辭雅與氣緊密相關。姚鼐〈復吳仲倫書〉云:「理當而格俊,氣清而辭雅。」其〈復魯絜非書〉謂:「吐辭雅馴不蕪」。
關於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暫時先講到這裡。大家以後再讀古文,感受或許和以前大有不同吧。
下期續。
本文由看新聞網原創、編譯或首發,並保留版權。轉載必須保持文本完整,聲明文章出自看新聞網並包含原文標題及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