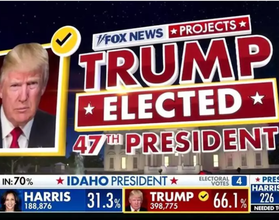人生只要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地度过就可以了!—– 无名氏
(六)
遇罗克行刑前居住的东四北大街西面靠明星电影院的小死胡同至今还在。
明星电影院已经没有了。明星电影院旁边的步行街隆福寺里的电影院工人剧乐部、蟾宫电影院还有。文革中蟾宫改成长虹,现在又改回来了,并翻盖得高大气派。
遇罗克看不到这一切,他被枪毙时只有27岁,他的生命定格在1970年3月5日,如果他不写“出身论”,在1966年八月法西斯纳粹红卫兵血洗北京平民时不选择挺身而出反抗的这条路,苟活至今,会是什么样?
在网上遇罗克的纪念园里,有几个女孩子写道:我们站在前排,是你的朋友,是你的爱人,……天堂里的他听得到吗?
那时候的北京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俗称“老三届”,基本上是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的一部分。遇罗克是1942年5月出生,比我们大几岁,北平“解放”的时候他已经7岁了,他在“解放前”生活的7年打下和我们从小被共产党洗脑长大的不一样的底,他有两位不同凡响的双亲,他自己聪颖好学,智商超人,让他在文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位伟人,一颗在黑暗天空中耀眼的星辰。
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北京城不是很大。东边是朝阳门、东直门,北边是安定门,西边是永定门,南面是大前门、崇文门。几个存在亦或被拆的门围着四四方方的内城区。
以地安门鼓楼、景山公园、故宫、天安门、前门为北京的中轴线,北海公园、团城、中南海在西面。中山公园在东面。天坛公园在南面。雍和宫在东南角。月坛在西面。
颐和园是远郊区了,要在西郊动物园换上二路长途汽车,票价很贵,每位二毛钱。小孩过了三尺以上就要打票。
动物园旁边有北京展览馆、莫斯科餐厅,对面有天文馆,是“解放后”在58年“大跃进”前后建的。文革中,各派“老三届”都以在莫斯科餐厅就餐为荣。
著名的风景区香山公园、坛柘寺、十三陵、八大岭、长城……都在比颐和园更远的西边。要坐专车才能去。
站在城里的中轴线制高点景山公园的煤山顶山环顾北京,一座庄严美丽肃穆的一座古城。文革中,共产党的二代法西斯红卫兵把它糟蹋得不成样子。
(七)
遇罗克行刑前居住的东四北大街西面靠明星电影院的小死胡同至今还在。
明星电影院已经没有了。明星电影院旁边的步行街隆福寺里的电影院工人剧乐部、蟾宫电影院还有。文革中蟾宫改成长虹,现在又改回来了,并翻盖得高大气派。
遇罗克看不到这一切,他被枪毙时只有27岁,他的生命定格在1970年3月5日,如果他不写“出身论”,在1966年八月法西斯纳粹红卫兵血洗北京平民时不选择挺身而出反抗的这条路,苟活至今,会是什么样?
在网上遇罗克的纪念园里,有几个女孩子写道:我们站在前排,是你的朋友,是你的爱人,……天堂里的他听得到吗?
那时候的北京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俗称“老三届”,基本上是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的一部分。遇罗克是1942年5月出生,比我们大几岁,北平“解放”的时候他已经7岁了,他在“解放前”生活的7年打下和我们从小被共产党洗脑长大的不一样的底,他有两位不同凡响的双亲,他自己聪颖好学,智商超人,让他在文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位伟人,一颗在黑暗天空中耀眼的星辰。
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北京城不是很大。东边是朝阳门、东直门,北边是安定门,西边是永定门,南面是大前门、崇文门。几个存在亦或被拆的门围着四四方方的内城区。
以地安门鼓楼、景山公园、故宫、天安门、前门为北京的中轴线,北海公园、团城、中南海在西面。中山公园在东面。天坛公园在南面。雍和宫在东南角。月坛在西面。
颐和园是远郊区了,要在西郊动物园换上二路长途汽车,票价很贵,每位二毛钱。小孩过了三尺以上就要打票。
动物园旁边有北京展览馆、莫斯科餐厅,对面有天文馆,是“解放后”在58年“大跃进”前后建的。文革中,各派“老三届”都以在莫斯科餐厅就餐为荣。
著名的风景区香山公园、坛柘寺、十三陵、八大岭、长城……都在比颐和园更远的西边。要坐专车才能去。
站在城里的中轴线制高点景山公园的煤山顶山环顾北京,一座庄严美丽肃穆的一座古城。文革中,共产党的二代法西斯红卫兵把它糟蹋得不成样子。
(八)
听说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称罗文为“罗文哥哥”。我听了很高兴,据说这位女士是位离异人士,是位工程师。
罗文单身一人,与一只猫一条狗住在诺大的庄园里,能在晚年找到真正的爱情,陪伴他度过往后的悠悠岁月,再好不过。
年轻的时候看过郑念女士写的“上海滩生死记”,听我的老师刘渭平先生告诉我,刘先生认识郑女士,本来都是中华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大陆易职后,刘先生时任国民政府驻澳大利亚悉尼的领事,回不去了,就全家移民澳洲生活下来。
郑女士则在大陆历经中国共产党各项运动的磨难,文化大革命中,女儿不幸被红卫兵折磨至死。她本人则九死一生逃离生天,移民海外,把自己的真实遭遇写成一部书,轰动一时。
晚年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她书中有一句话说:“爱情比孩子更重要。”我当时很不理解,活到现在,在心灵深处,发现想情人远比想孩子多。
我有一个对我无话不谈的哥们儿,他比我小不了两岁,依然在执着地追求爱情,像年轻人一样徒步远行,风尘仆仆,口甘舌燥,百死而无一悔,我听他描述朝圣过程,实在理解并感动。
老年人对爱情的渴望远胜于年轻人,因为岁月的沉积告诉老年人真爱是什么样的,真爱的稀有与可贵。得到就得到了,没得到也许就永远得不到了,因为没有多少时间了!
我想我是真爱过罗文的,他爱我则是在他第二次离婚后,他在微信里称我:“我的挚爱…”
当年我一厢情愿爱他的时候,他一心扑在反“血统论”上,上上次打电话,他还说:“我那时候不需要。”
我那时候也没有任何需要,只是单纯的爱他。我一直很敬佩他,他始终在我眼里,是个最勇敢的人,是个英雄,一个自始至终与专制暴政做斗争的人,一个为中国草根人民说话的人。
我那时才18岁,我没看错他。他永远是我最值得信任的朋友之一。
对我而言,文化大革命是在1966年6月2日开始的。因为校园里出现了我们班政治老师杨振率领十三名高干子弟给校领导贴的大字报,指责校领导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从那天开始,再也没恢复正常的上课,社会正常秩序大崩盘,愈演愈烈,这一拖就是整整十年。
我也是在那时候发现,我们被从小灌输的理论全不管用,全是扯蛋!怎么活下去呢?靠什么往下走呢?
周围的同学都在争着当左派,认为左派是革命的,宁左勿右,即使犯了错误,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等等,扯不清,理还乱,怎么着都不对,怎么着都不行。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开始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以前我就是随大流,社会学校让我怎么走我就怎么走,我从小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好孩子好学生。
那时候是6月,我强烈地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在装丫挺,演戏,装给别人看,证明自己不是自己,是某种势力要求你做的那样的人。
我懒得装,那样太累了不说,对我而言是一种虽生犹死的事情。
(九)
我从徐家祯先生那儿听到过一个词,说:“共产党每次运动都是关起门来打狗,他们自己说的。”
“关起门来打狗”够形象的,No way out ! 躲没地方躲,藏没地方藏,该打死的打死,该打伤的打伤,该劳改的劳改,该收监的收监,只有坐以待毙的份!
记得在北京1978年认识民间地下刊物“四五论坛”创始人之一刘青时,和他曾讨论过遇罗克有没有生存的机会?刘青自信地说:“那时候不行,天罗地网,现在就可以逃跑!”我疑惑地问:“能跑到哪儿?”“哪儿都可以,外地、农村、大山深处……”
轮到他自己的时候(为魏京生一案),他不但没跑,还为了使被捕的朋友脱险,主动去北京市公安局自首。一关押就是十年之久。
“运动”是共产主义“大洋国”特有又日常的生活形态。对比在国外几十年的生活,更感到中共国的窒息与恐惧。对特权阶层是天堂,对平民是地狱。
初来澳洲,徐家祯先生对我说,他是“苦海余生”,三十多年后,我问他记不记得,他说:“不是苦海余生,是虎口余生!”谁又不是!!!
其实还有一条路—自杀。文化大革命6月份开始,我觉得生活变得特别无聊,不好玩,呼吸困难,我想过自杀。一闪而过,并不深刻,更谈不上付之行动。而且觉得这种念头可耻。
这个念头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罗文的前妻张富英。她和张君若、王玲是在中学文革报第五期加入的。
1968年一月以后,有一次,我和她一边走一边谈,她突然问我:“你想过自杀吗?”“想过,你呢?”“我也想过。”她回答。
那次她还对我说:“你要想找比罗文更高的,我认识,可以给你介绍。”
我心想:“我看上罗文可不是为这个!”
对男孩,我从不以貌取人。
我知道想过自杀并想付诸行动的还有中学文革报创始人之一牟志京,牟志京亲口讲给许多人听过。我是其中之一。他们男四中和我们师大女附中是北京最负盛名的两个中学。据说我们学校的大部分人马是共产党老区带过来的,所以高干子弟多。四中平民子弟多是勤奋饱学之士,高干子弟多是被塞进去的。
两个学校的政治空气一个比一个浓。
我1964年考入女附中高中,一进去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先搞暴露思想,后搞学习雷锋。但没听说哪个学生挨整。
四中挺邪乎,学生分成几等,左、中、右。文革中,我打听一个妈妈同事的小孩,和我史家胡同小学同学、高我一级的张力行是哪一等?回答是:“当然是右派学生了!”
牟志京也当仁不让地被划在“右派学生”里,最让他受不了的是他们偷看了他的日记,说他“爱情至上”,他决定自杀,掏出兜里仅有的二元钱,准备大吃一顿,自裁了事。
罗文对他的故事付之一笑,对我说:“两块钱叫什么大吃一顿!”
这些运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热身、前奏,全北京市的中学都在开展政治思想教育,抓阶级斗争,草木皆兵,杯弓蛇影,疑神疑鬼,把杂志上的风景看成“蒋介石万岁”,凡此种种,人心惶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树欲静而风不止”,势不可挡。
现在的台海风云让我感到大有当年的劲头。
我总想:“文革为什么没人出来制止呢?非要’八亿人不斗行吗?'(毛泽东语)”
八亿人互掐一场,死伤无数,国家差点崩溃。有谁落着好了。
“还有谁比这被否定的更快的,人一死,家就被端了!”后来的北京大学一级哲学教授张祥龙1976年12月在我家对我和赵京兴说。
惨痛的前车之鉴,不可闭目塞听,重蹈覆辙!!!
(未完待续)

本文由看新闻网原创、编译或首发,并保留版权。转载必须保持文本完整,声明文章出自看新闻网并包含原文标题及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