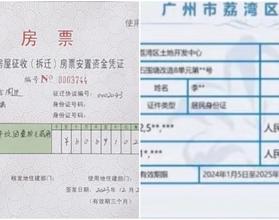韩信用兵如神,为大汉立下汗马功劳,可谓无韩信则汉不能得天下。他被诬谋反,三族遭夷,引无数人同情叹息。韩信之才华功绩光照千古,无人否认,而有争议之处,在于是否谋乱。有人以为谋乱证据确凿,依据是《史记·淮阴侯列传》。然而,阅读任何史料,都不应尽信之;且《史记》微言大义,司马迁将对韩信谋乱的怀疑与否定隐于文中,需细读方知其深意。以下解读原文。
《史记·淮阴侯列传》记武涉、蒯通劝韩信叛汉之言尤详,均遭韩信拒绝。当时假如选择叛变,是最佳时机,那时尚不忍见利背义,为何到天下一统、最不适宜叛变的时候谋反?
〈淮阴侯列传〉云:“楚已亡龙且,项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勠力击秦。秦已破,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今释此时,而自必于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韩信谢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当时韩信已被刘邦封为齐王,其地位与才力足以左右楚汉胜败存亡,倘若脱汉而三分天下,亦可实现。且武涉言及项王若亡,则刘邦必将矛头指向韩信,此亦在预料之中。而韩信答复道,汉王“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就算死也不叛变,态度坚决如是。

蒯通之言更具说服力,他的辩才很好,而且是韩信身边的谋士。〈淮阴侯列传〉以很大篇幅记述蒯、韩之间的对话:
“武涉已去,齐人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以相人说韩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韩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对曰:‘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韩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对曰:‘愿少闲。’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韩信曰:‘何谓也?’蒯通曰:‘天下初发难也,俊雄豪桀建号壹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遝,熛至风起。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于中野,不可胜数。楚人起彭城,转鬬逐北,至于荥阳,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闲,迫西山而不能进者,三年于此矣。汉王将数十万之众,距巩、雒,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荥阳,伤成皋,遂走宛、叶之闲,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夫锐气挫于险塞,而粮食竭于内府,百姓罢极怨望,容容无所倚。以臣料之,其势非天下之贤圣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两主之命县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愿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能用也。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彊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彊,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孰虑之。’”
二人深入交谈前,先命左右之人回避。蒯通之言,虽是挑拨,却也近乎推心置腹。而韩信依然不动摇,说道:
“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
蒯通进一步劝说道:“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始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后争张黡、陈泽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项王,奉项婴头而窜,逃归于汉王。汉王借兵而东下,杀成安君泜水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下笑。此二人相与,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黡、陈泽。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于句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愿足下深虑之。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臣请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
趋利和避害两大角度,都说得理据充足。韩信此时的回复是:“谢曰:‘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

几天后,蒯通又敦促韩信快做决定,说:“‘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跼躅,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喑聋之指麾也’。此言贵能行之。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愿足下详察之。”
此时,韩信的回应是:“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最终拒绝蒯通,坚持不叛。
为韩信作传,蒯通劝叛之言不必如此详写,而司马迁之所以这样写,是为了表现韩信的忠心与知恩图报,言外之意是质疑韩信后来谋反的真实性。对此,方苞〈书淮阴侯列传后〉评论道:
“其详载武涉、蒯通之言,则微文以志痛也。方信据全齐,军锋震楚、汉,不忍乡利倍义,乃谋畔于天下既集之后乎?”
史书详略鲜明之处,往往是读者需深思之处。方苞认为,司马迁有意在此处含蓄表达自己的沉痛,暗示韩信蒙冤。时机最佳之时,面对如此大的诱惑而不反,更不可能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反。
韩信后来被指控谋反,共有两次,第一次的结果是被赦免,第二次的结果是被杀。两次都有疑点,疑似均为诬告。
第一次被告前,项羽已败,刘邦收夺韩信的军队,改封韩信为楚王。〈淮阴侯列传〉云:
“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汉五年正月,徙齐王信为楚王,都下邳。……项王亡将锺离眛家在伊庐,素与信善。项王死后,亡归信。汉王怨眛,闻其在楚,诏楚捕眛。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
项羽兵败,外患既除,刘邦有精力针对功高震主的韩信。韩信生于楚地,被封为楚王相当于衣锦还乡,若从此安度馀生,可谓无憾矣。刘邦这样安排,有防范的用意。且韩信已失兵权,在楚地有何条件与理由谋反?林西仲评论:“大抵淮阴欲反,当在王齐时,至楚则已难矣。”如果韩信要反,不可能不知自己具备的条件多么不足。
“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告发者的依据是甚么?〈淮阴侯列传〉虽然说“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但没有明确表明因果关系。而《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写道:“徙楚,坐擅发兵,废为淮阴侯。”罪名是“擅发兵”,或许与韩信“行县邑,陈兵出入”有关。然而,即使陈兵进出县邑,也不能据此断定谋反。

锺离眜曾是项王的部下,与韩信交好,后来投奔韩信,刘邦对他恨之入骨。据〈淮阴侯列传〉,韩信被告谋反后,为讨好刘邦,拿锺离眜的人头献媚。此事可信否?《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载,汉五年九月,“王得故项羽将锺离眜,斩之以闻。”而告韩信谋反的时间在汉六年,之后韩信与锺离眜商量将他的首级献给刘邦,于是锺离眜怒骂韩信,愤而自尽,显然相矛盾。若锺离眜已于汉五年被斩,怎可能活著与韩信交谈?韩信逼死锺离眜一事,真实性颇为可疑。
第一次所谓“谋反”,最后以赦免告终。〈淮阴侯列传〉云:“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雒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如果刘邦掌握韩信谋反的确凿证据,不会赦免他,应只是有人诬告,刘邦大抵也明白韩信未反,但借此机会警告,顺便有借口进一步削弱韩信。
韩信被贬为淮阴侯后,不能到自己的封地,无实权,无兵符,无印玺,心中也清楚刘邦猜忌自己,经常以生病为由不朝。落至此等境地,拿甚么反?《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第二次“谋反”,亦颇可疑:
“陈豨拜为钜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豨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彊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锺室。”
疑点如下:
1、韩信拉著陈豨的手,令左右旁人回避后说的话,谁听到了?此一疑点,方苞已指出:“其与陈豨辟人挈手之语,孰闻之乎?”
2、韩信不具备袭击吕后和太子的能力。假传诏书,调动衙门里的奴仆,组成一支军队,韩信不知道这极不现实吗?假使能调动徒奴,一共能有多少人?韩信会那么傻?方苞曰:“无符玺节篆,而欲‘与家臣夜诈诏,发诸官徒奴’,孰听之乎?”林西仲曰:“夫帝之自将讨豨也,岂不计及雒阳为根本重地,而使吕后、太子拥重兵以居守乎?……既无兵权,即尽赦诸官徒奴,为数几何?”
3、仅凭一人之辞,证据不足,先斩后奏。韩信有一个门客犯了罪,韩信要杀该门客,其弟向吕后告韩信谋反,此人之言可信度能高吗?方苞曰:“未闻谳狱而明征其辞,所据乃告变之诬耳。”没有审理过程,没有对证,且不待刘邦回来后再判生死。假如韩信谋叛,那么,和他一起策划的家臣、暗中派遣到陈豨处的送信人下场如何?却未见有逮捕并处置逆党各人的记载。林西仲有一段分析:“乃从令之部署不问也,定谋之家臣不问也,即使至豨所之人,亦不问也。岂法可加于无辜之三族,独宽于共事之腹心?无是理也。是知舍人弟之告变,乃吕后阴使之如告彭越故事,因而又致其词无疑矣。”
可知,韩信第二次所谓“谋反”,也是一起冤案。

《史记·淮阴侯列传》写到韩信之死,尚未结束,后面还讲了一件事。在史书中你会经常看到,按理说应该收束的地方,其后又补充事件或细节。〈淮阴侯列传〉写道:
“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问:‘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计。’高祖曰:‘是齐辩士也。’乃诏齐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
刘邦返回京城后,得知韩信被杀,心情是“且喜且怜之”,此五字值得细品。林西仲评论:“且喜且怜之,亦知其无罪受戮,为可悯也。”
刘邦又得知蒯通曾教唆韩信谋反,要烹他,他喊冤,一番话竟使得刘邦赦了他。司马迁有意透过对比,含蓄地为韩信鸣不平——有罪的蒯通能得原谅,屡立奇功而无罪的韩信却不能。方苞评曰:“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释,况定齐而求自王,灭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减乎?故以通之语终焉。”

最后就是赞,即“太史公曰”。如下: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司马迁亲自到淮阴看过。当地人告诉他,韩信还是平民时就与众不同,其母亲去世后,他没钱埋葬,但仍把棺材埋在高敞地,使四周空地上以后能有千家万户居住。司马迁亲眼见到韩母的坟,确实如此。
之后司马迁对韩信的评价,看似责怪,实则另有深意,是为韩信鸣冤。他说,韩信如果能学道家,“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就更好了,堪比周朝的周公、召公、太公,世世代代享受祭祀。然而他在天下已定后谋反,导致灭族,岂不是应该的?司马迁在这里用的是“反言”笔法,这是中国古书中常见的笔法之一。司马迁并非真认为韩信谋乱,方苞对此解释:“后论似果以信为叛逆者,盖其诬于传具之矣,故反言以见义,谓天下已集,非可以叛逆之时矣。若果谋此,虽族诛亦宜,然以信之智,而肯出此乎?”
看过方苞的解读后,各位不妨现在再读一遍《史记》这段文字:“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再度品味,有何滋味?司马迁这段“太史公曰”,直击读者内心深处,用“反言”营造的引人同情与讽刺的效果,胜过其他表达方式。在此引用李笠的评语:“读此数语,韩信心迹,刘季、吕雉手段,昭然若揭矣。文家反复辨论,反不若此言之宛转痛快。”
或问,司马迁为何写得如此隐晦?为何不直接删掉他怀疑的部分,以直白的文字为韩信平反?首先,即使在刘邦死后,做臣子的也很难为韩信平反,风险太大;其次,史家向来有一原则,即《穀梁传》所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自己认为可信的和可疑的,都要传给后人,尽量客观。大抵司马迁看到的部分史料已非事实,他又不能目睹真相,所以韩信“谋反”的事,也写下来。
《史记》中与〈淮阴侯列传赞〉形成对比的,是〈萧相国世家赞〉。评价萧何,亦是一段微词:
“太史公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
汉初诸功臣,刘邦只能容像闳夭、散宜生那样的,而容不得周公、召公、太公之辈。韩信诛灭,萧何显赫,有奇节岂不如无奇节?讽刺之意味,昭然若揭。
本文由看新闻网原创、编译或首发,并保留版权。转载必须保持文本完整,声明文章出自看新闻网并包含原文标题及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