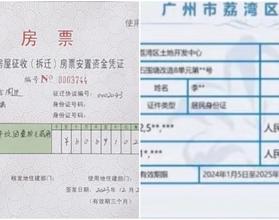韓信用兵如神,為大漢立下汗馬功勞,可謂無韓信則漢不能得天下。他被誣謀反,三族遭夷,引無數人同情嘆息。韓信之才華功績光照千古,無人否認,而有爭議之處,在於是否謀亂。有人以為謀亂證據確鑿,依據是《史記·淮陰侯列傳》。然而,閱讀任何史料,都不應盡信之;且《史記》微言大義,司馬遷將對韓信謀亂的懷疑與否定隱於文中,需細讀方知其深意。以下解讀原文。
《史記·淮陰侯列傳》記武涉、蒯通勸韓信叛漢之言尤詳,均遭韓信拒絕。當時假如選擇叛變,是最佳時機,那時尚不忍見利背義,為何到天下一統、最不適宜叛變的時候謀反?
〈淮陰侯列傳〉云:「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勠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
當時韓信已被劉邦封為齊王,其地位與才力足以左右楚漢勝敗存亡,倘若脫漢而三分天下,亦可實現。且武涉言及項王若亡,則劉邦必將矛頭指向韓信,此亦在預料之中。而韓信答覆道,漢王「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就算死也不叛變,態度堅決如是。

蒯通之言更具說服力,他的辯才很好,而且是韓信身邊的謀士。〈淮陰侯列傳〉以很大篇幅記述蒯、韓之間的對話:
「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仆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捲,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閒,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遂走宛、葉之閒,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
二人深入交談前,先命左右之人迴避。蒯通之言,雖是挑撥,卻也近乎推心置腹。而韓信依然不動搖,說道:
「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
蒯通進一步勸說道:「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
趨利和避害兩大角度,都說得理據充足。韓信此時的回覆是:「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

幾天後,蒯通又敦促韓信快做決定,說:「『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喑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
此時,韓信的回應是:「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最終拒絕蒯通,堅持不叛。
為韓信作傳,蒯通勸叛之言不必如此詳寫,而司馬遷之所以這樣寫,是為了表現韓信的忠心與知恩圖報,言外之意是質疑韓信後來謀反的真實性。對此,方苞〈書淮陰侯列傳後〉評論道:
「其詳載武涉、蒯通之言,則微文以志痛也。方信據全齊,軍鋒震楚、漢,不忍鄉利倍義,乃謀畔於天下既集之後乎?」
史書詳略鮮明之處,往往是讀者需深思之處。方苞認為,司馬遷有意在此處含蓄表達自己的沉痛,暗示韓信蒙冤。時機最佳之時,面對如此大的誘惑而不反,更不可能在最不利的情況下反。
韓信後來被指控謀反,共有兩次,第一次的結果是被赦免,第二次的結果是被殺。兩次都有疑點,疑似均為誣告。
第一次被告前,項羽已敗,劉邦收奪韓信的軍隊,改封韓信為楚王。〈淮陰侯列傳〉云:
「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項王亡將鍾離眛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
項羽兵敗,外患既除,劉邦有精力針對功高震主的韓信。韓信生於楚地,被封為楚王相當於衣錦還鄉,若從此安度餘生,可謂無憾矣。劉邦這樣安排,有防範的用意。且韓信已失兵權,在楚地有何條件與理由謀反?林西仲評論:「大抵淮陰欲反,當在王齊時,至楚則已難矣。」如果韓信要反,不可能不知自己具備的條件多麼不足。
「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告發者的依據是甚麼?〈淮陰侯列傳〉雖然說「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但沒有明確表明因果關係。而《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寫道:「徙楚,坐擅發兵,廢為淮陰侯。」罪名是「擅發兵」,或許與韓信「行縣邑,陳兵出入」有關。然而,即使陳兵進出縣邑,也不能據此斷定謀反。

鍾離眜曾是項王的部下,與韓信交好,後來投奔韓信,劉邦對他恨之入骨。據〈淮陰侯列傳〉,韓信被告謀反後,為討好劉邦,拿鍾離眜的人頭獻媚。此事可信否?《史記·秦楚之際月表》記載,漢五年九月,「王得故項羽將鍾離眜,斬之以聞。」而告韓信謀反的時間在漢六年,之後韓信與鍾離眜商量將他的首級獻給劉邦,於是鍾離眜怒罵韓信,憤而自盡,顯然相矛盾。若鍾離眜已於漢五年被斬,怎可能活著與韓信交談?韓信逼死鍾離眜一事,真實性頗為可疑。
第一次所謂「謀反」,最後以赦免告終。〈淮陰侯列傳〉云:「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如果劉邦掌握韓信謀反的確鑿證據,不會赦免他,應只是有人誣告,劉邦大抵也明白韓信未反,但藉此機會警告,順便有藉口進一步削弱韓信。
韓信被貶為淮陰侯後,不能到自己的封地,無實權,無兵符,無印璽,心中也清楚劉邦猜忌自己,經常以生病為由不朝。落至此等境地,拿甚麼反?《史記·淮陰侯列傳》記載韓信第二次「謀反」,亦頗可疑:
「陳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疑點如下:
1、韓信拉著陳豨的手,令左右旁人迴避後說的話,誰聽到了?此一疑點,方苞已指出:「其與陳豨辟人挈手之語,孰聞之乎?」
2、韓信不具備襲擊呂后和太子的能力。假傳詔書,調動衙門裡的奴僕,組成一支軍隊,韓信不知道這極不現實嗎?假使能調動徒奴,一共能有多少人?韓信會那麼傻?方苞曰:「無符璽節篆,而欲『與家臣夜詐詔,發諸官徒奴』,孰聽之乎?」林西仲曰:「夫帝之自將討豨也,豈不計及雒陽為根本重地,而使呂后、太子擁重兵以居守乎?……既無兵權,即盡赦諸官徒奴,為數幾何?」
3、僅憑一人之辭,證據不足,先斬後奏。韓信有一個門客犯了罪,韓信要殺該門客,其弟向呂后告韓信謀反,此人之言可信度能高嗎?方苞曰:「未聞讞獄而明徵其辭,所據乃告變之誣耳。」沒有審理過程,沒有對證,且不待劉邦回來後再判生死。假如韓信謀叛,那麼,和他一起策劃的家臣、暗中派遣到陳豨處的送信人下場如何?卻未見有逮捕並處置逆黨各人的記載。林西仲有一段分析:「乃從令之部署不問也,定謀之家臣不問也,即使至豨所之人,亦不問也。豈法可加於無辜之三族,獨寬於共事之腹心?無是理也。是知舍人弟之告變,乃呂后陰使之如告彭越故事,因而又致其詞無疑矣。」
可知,韓信第二次所謂「謀反」,也是一起冤案。

《史記·淮陰侯列傳》寫到韓信之死,尚未結束,後面還講了一件事。在史書中你會經常看到,按理說應該收束的地方,其後又補充事件或細節。〈淮陰侯列傳〉寫道:
「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劉邦返回京城後,得知韓信被殺,心情是「且喜且憐之」,此五字值得細品。林西仲評論:「且喜且憐之,亦知其無罪受戮,為可憫也。」
劉邦又得知蒯通曾教唆韓信謀反,要烹他,他喊冤,一番話竟使得劉邦赦了他。司馬遷有意透過對比,含蓄地為韓信鳴不平——有罪的蒯通能得原諒,屢立奇功而無罪的韓信卻不能。方苞評曰:「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釋,況定齊而求自王,滅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減乎?故以通之語終焉。」

最後就是贊,即「太史公曰」。如下: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司馬遷親自到淮陰看過。當地人告訴他,韓信還是平民時就與眾不同,其母親去世後,他沒錢埋葬,但仍把棺材埋在高敞地,使四周空地上以後能有千家萬戶居住。司馬遷親眼見到韓母的墳,確實如此。
之後司馬遷對韓信的評價,看似責怪,實則另有深意,是為韓信鳴冤。他說,韓信如果能學道家,「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就更好了,堪比周朝的周公、召公、太公,世世代代享受祭祀。然而他在天下已定後謀反,導致滅族,豈不是應該的?司馬遷在這裡用的是「反言」筆法,這是中國古書中常見的筆法之一。司馬遷並非真認為韓信謀亂,方苞對此解釋:「後論似果以信為叛逆者,蓋其誣於傳具之矣,故反言以見義,謂天下已集,非可以叛逆之時矣。若果謀此,雖族誅亦宜,然以信之智,而肯出此乎?」
看過方苞的解讀後,各位不妨現在再讀一遍《史記》這段文字:「於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再度品味,有何滋味?司馬遷這段「太史公曰」,直擊讀者內心深處,用「反言」營造的引人同情與諷刺的效果,勝過其他表達方式。在此引用李笠的評語:「讀此數語,韓信心跡,劉季、呂雉手段,昭然若揭矣。文家反覆辨論,反不若此言之宛轉痛快。」
或問,司馬遷為何寫得如此隱晦?為何不直接刪掉他懷疑的部分,以直白的文字為韓信平反?首先,即使在劉邦死後,做臣子的也很難為韓信平反,風險太大;其次,史家向來有一原則,即《穀梁傳》所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自己認為可信的和可疑的,都要傳給後人,儘量客觀。大抵司馬遷看到的部分史料已非事實,他又不能目睹真相,所以韓信「謀反」的事,也寫下來。
《史記》中與〈淮陰侯列傳贊〉形成對比的,是〈蕭相國世家贊〉。評價蕭何,亦是一段微詞: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勛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漢初諸功臣,劉邦只能容像閎夭、散宜生那樣的,而容不得周公、召公、太公之輩。韓信誅滅,蕭何顯赫,有奇節豈不如無奇節?諷刺之意味,昭然若揭。
本文由看新聞網原創、編譯或首發,並保留版權。轉載必須保持文本完整,聲明文章出自看新聞網並包含原文標題及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