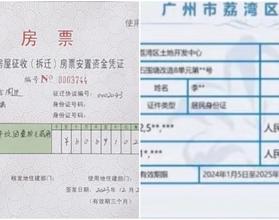我是第二次走近开平碉楼了。
最初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乘车经过四邑的开平县,远看沿路的田野上疏疏落落左一幢右一幢冒出灰青厚实的碉楼,好一幅奇特的景观。得知这是广东侨乡开平的文化身份,便留下了一份好奇心。
出国多年后,才第一次有机会走近开平碉楼。那是新世纪进入第三年,令世界震惊的 “非典”刚平息,人们对这片大地还心有余悸,我们一些海外作家受邀回故国看看,东南西北实地走一圈。没想到,我们的第一站,就是开平碉楼的自立村。

十年后的如今,也是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收敛之后,藉着国际学术研讨会之际,我又第二次走进开平碉楼。此时虽说11月已入冬,但南粤大地仍如仲夏,暖意融融。我们走进开平侨乡,触摸碉楼、古镇,侨味的热度迎面扑鼻。
与上次不同,此时的开平碉楼已申遗成功,成了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籍的美国旧金山作家陈绮屏曾对我说,她家的碉楼,六十年代已经坍塌,家族里的一些人把里面的坤甸梁柱等拆卖了。当年建造的三千多座碉楼,现仅存一千八百多座,能经受得起时间淘洗及世俗诱惑而留下来的都是宝啊,这是一面历史镜像。
这面镜里,会看到什么呢?
走进马降龙村,静悄悄的,古旧的青砖瓦房排列整整齐齐,大门上还有广彩雕刻,难得见到几个老妇,悠悠闲闲在养鹅种瓜。也难怪,几十万的开平人,还比不上境外的开平人呢,据说自开平飘洋过海的华人先后就有二百四十万人。与上次参观的自力村的自然状态不同,马降龙已处于开发保护的状态,经过修葺整理,成为游客景点。不过,还是修旧如旧,还是保留了村民的生活状态,只是多了点整洁清新,多了点游客指南。
近看碉楼,原来都是青砖砌起的碉堡状的家居高楼。这些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碉楼,厚墙铁窗,布满枪眼,楼内生活用品一应俱全,那是躲着防范绑匪的。当年那些落叶归根的华侨揣着沉甸甸的血汗金条荣归故里,自然成了土匪洗劫的目标。跨过沉重的铁门进入碉楼,看到墙上褪色的主人家庭照片,看到室内蒙尘的舶来品,似乎走进了时光隧道,看到了历史影像。
在碉楼里,碰上正下楼的北美作家黄宗之,他嚷着,这楼梯怎么是水泥的呢,肯定是新铺的。我笑说,这是一百年前的原汁原味啊。一般中国旧房的楼梯多是木的,可这是侨乡,当年华侨就把西方的建筑材料引进回乡了。你看碉楼铁门的黑色钢板,德国货;乳白的抽水马桶,英国货;彩色的地板瓷砖,也是意大利的;进口水泥(广东人叫洋灰、红毛泥)更不在话下。就是建筑设计,也是中西合璧。下面是传统的碉堡外形,方正密实,上面则有欧式的城堡构件,如古希腊的柱廊,或古罗马的柱式,也有中世纪的哥特式尖拱,连楼顶也雕刻着猎鹰作保护神。这就是华侨乡民开放式的环境意识、风水观念和审美趣味的混合物。
作家们兴趣盎然,有人围着碉楼四周打转,有人楼上楼下仔细端详,有人拿着相机拍个不停,也有三三两两探讨着什么。记得上一次在自力村碉楼参观时,作家们也是诗兴大发,说碉楼里有爱恨情仇,有飘洋过海,有抗日杀敌,完全可以写部可歌可泣的电视连续剧嘛。大家七嘴八舌把故事、人物、场景东拼西凑都拉扯得七七八八八了,可是说归说,最后也没见啥动静。倒是同行的加拿大作家张翎,看得多说得少,之后不声不响几次重访碉楼,真的写下了从碉楼走出的女性在大洋彼岸淘金路上踉踉跄跄的长篇小说《金山》,不仅叫好又叫座,还拿了个大奖。 我想,今次又会有谁酝酿出什么大作品呢?至少,在回程的巴士上,洛杉矶作家施玮就深情朗诵碉楼激发她灵感的诗作。
如今看似平静的碉楼,细细品味,有生活的痛苦,有乡土的眷念,有建筑风格的亮丽。每一座碉楼,都是一面历史镜像,留下侨乡岁月的痕迹,稍稍用心,都能感触到她的体温,她的灵魂。
同样是侨乡历史镜像的还有开平赤坎古镇。今次重游,倒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滋味。

今日的赤坎,以骑楼街著称。遮阳挡雨的骑楼街,是华侨从南洋带回来的建筑设计理念,形成了岭南建筑的一种风格。我小时候就是在广州的骑楼街穿梭奔跑长大的。随着新时代城市开发,骑楼街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便是时尚商厦。而赤坎骑楼街的保存,则显得格外珍贵了。
八十年代我曾乘车经过赤坎。开平县城虽已从赤坎迁离,但延绵的骑楼街仍很喧闹,骑楼里店铺林立,骑楼下摆满了单车。汽车在弯曲窄小的街上小心穿行,两旁全是地摊小贩,虽然拥挤,却也热闹人气旺。我恍惚回到儿时广州生活的情景。可今天的赤坎古镇,已有点面目全非,再也不是人声车声鸡叫狗吠的生活小镇了,而成了旅游景点、电影片场。

赤坎的骑楼街,只保留了潭江边的一段,其余的都是扩建或仿造,规模明显扩充,欧陆风情的房子也醒目了很多。但整个镇已不是普通民众的生活区了,而是十足十的对游客开放的旅游景区。拿着入场门劵走在镇上,闻不到熟悉的烟火味,看到的都是仿制的民国招牌。如果在拍摄《三家巷》《廖仲恺》《让子弹飞》《一代宗师》等影视作品,倒也能传导出某种历史情景,但我亲身走在这现场实景中,崭新的古董有轨车叮咚作响擦身而过,强大功率的喇叭蹦出震耳的歌声混杂着空气中的啤酒香味,却无法找到那种历史情怀,明显感受到的是一种游乐场的氛围。当然,这只是我很个人的感受。毕竟,我当年曾见识过日常人烟的赤坎,期望能再次领略到文化保护下生气勃勃的赤坎。但有点失落了。
对于历史文化遗存,究竟是保持自然原生态,修旧如旧好呢,还是扩大规模,仿建新造,营造气势好呢?我很困惑。透过历史镜像,那种看相陈旧,那种痕迹斑驳,那种不完美却又独特的形态,不正是历史的记忆,文化的印痕,历史文化遗存的价值所在吗?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自然状态、原汁原味,看似不起眼,却又独一无二、意蕴丰富的碉楼。你说呢?
本文由看新闻网原创、编译或首发,并保留版权。转载必须保持文本完整,声明文章出自看新闻网并包含原文标题及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