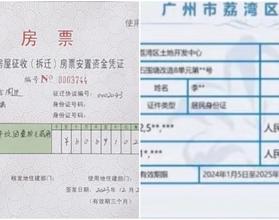我是第二次走近開平碉樓了。
最初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我乘車經過四邑的開平縣,遠看沿路的田野上疏疏落落左一幢右一幢冒出灰青厚實的碉樓,好一幅奇特的景觀。得知這是廣東僑鄉開平的文化身份,便留下了一份好奇心。
出國多年後,才第一次有機會走近開平碉樓。那是新世紀進入第三年,令世界震驚的 「非典」剛平息,人們對這片大地還心有餘悸,我們一些海外作家受邀回故國看看,東南西北實地走一圈。沒想到,我們的第一站,就是開平碉樓的自立村。

十年後的如今,也是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收斂之後,藉着國際學術研討會之際,我又第二次走進開平碉樓。此時雖說11月已入冬,但南粵大地仍如仲夏,暖意融融。我們走進開平僑鄉,觸摸碉樓、古鎮,僑味的熱度迎面撲鼻。
與上次不同,此時的開平碉樓已申遺成功,成了世界文化遺產。開平籍的美國舊金山作家陳綺屏曾對我說,她家的碉樓,六十年代已經坍塌,家族裡的一些人把裡面的坤甸樑柱等拆賣了。當年建造的三千多座碉樓,現僅存一千八百多座,能經受得起時間淘洗及世俗誘惑而留下來的都是寶啊,這是一面歷史鏡像。
這面鏡里,會看到什麼呢?
走進馬降龍村,靜悄悄的,古舊的青磚瓦房排列整整齊齊,大門上還有廣彩雕刻,難得見到幾個老婦,悠悠閒閒在養鵝種瓜。也難怪,幾十萬的開平人,還比不上境外的開平人呢,據說自開平飄洋過海的華人先後就有二百四十萬人。與上次參觀的自力村的自然狀態不同,馬降龍已處於開發保護的狀態,經過修葺整理,成為遊客景點。不過,還是修舊如舊,還是保留了村民的生活狀態,只是多了點整潔清新,多了點遊客指南。
近看碉樓,原來都是青磚砌起的碉堡狀的家居高樓。這些建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碉樓,厚牆鐵窗,布滿槍眼,樓內生活用品一應俱全,那是躲着防範綁匪的。當年那些落葉歸根的華僑揣着沉甸甸的血汗金條榮歸故里,自然成了土匪洗劫的目標。跨過沉重的鐵門進入碉樓,看到牆上褪色的主人家庭照片,看到室內蒙塵的舶來品,似乎走進了時光隧道,看到了歷史影像。
在碉樓里,碰上正下樓的北美作家黃宗之,他嚷着,這樓梯怎麼是水泥的呢,肯定是新鋪的。我笑說,這是一百年前的原汁原味啊。一般中國舊房的樓梯多是木的,可這是僑鄉,當年華僑就把西方的建築材料引進回鄉了。你看碉樓鐵門的黑色鋼板,德國貨;乳白的抽水馬桶,英國貨;彩色的地板瓷磚,也是意大利的;進口水泥(廣東人叫洋灰、紅毛泥)更不在話下。就是建築設計,也是中西合璧。下面是傳統的碉堡外形,方正密實,上面則有歐式的城堡構件,如古希臘的柱廊,或古羅馬的柱式,也有中世紀的哥特式尖拱,連樓頂也雕刻着獵鷹作保護神。這就是華僑鄉民開放式的環境意識、風水觀念和審美趣味的混合物。
作家們興趣盎然,有人圍着碉樓四周打轉,有人樓上樓下仔細端詳,有人拿着相機拍個不停,也有三三兩兩探討着什麼。記得上一次在自力村碉樓參觀時,作家們也是詩興大發,說碉樓里有愛恨情仇,有飄洋過海,有抗日殺敵,完全可以寫部可歌可泣的電視連續劇嘛。大家七嘴八舌把故事、人物、場景東拼西湊都拉扯得七七八八八了,可是說歸說,最後也沒見啥動靜。倒是同行的加拿大作家張翎,看得多說得少,之後不聲不響幾次重訪碉樓,真的寫下了從碉樓走出的女性在大洋彼岸淘金路上踉踉蹌蹌的長篇小說《金山》,不僅叫好又叫座,還拿了個大獎。 我想,今次又會有誰醞釀出什麼大作品呢?至少,在回程的巴士上,洛杉磯作家施瑋就深情朗誦碉樓激發她靈感的詩作。
如今看似平靜的碉樓,細細品味,有生活的痛苦,有鄉土的眷念,有建築風格的亮麗。每一座碉樓,都是一面歷史鏡像,留下僑鄉歲月的痕跡,稍稍用心,都能感觸到她的體溫,她的靈魂。
同樣是僑鄉歷史鏡像的還有開平赤坎古鎮。今次重遊,倒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滋味。

今日的赤坎,以騎樓街著稱。遮陽擋雨的騎樓街,是華僑從南洋帶回來的建築設計理念,形成了嶺南建築的一種風格。我小時候就是在廣州的騎樓街穿梭奔跑長大的。隨着新時代城市開發,騎樓街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便是時尚商廈。而赤坎騎樓街的保存,則顯得格外珍貴了。
八十年代我曾乘車經過赤坎。開平縣城雖已從赤坎遷離,但延綿的騎樓街仍很喧鬧,騎樓里店鋪林立,騎樓下擺滿了單車。汽車在彎曲窄小的街上小心穿行,兩旁全是地攤小販,雖然擁擠,卻也熱鬧人氣旺。我恍惚回到兒時廣州生活的情景。可今天的赤坎古鎮,已有點面目全非,再也不是人聲車聲雞叫狗吠的生活小鎮了,而成了旅遊景點、電影片場。

赤坎的騎樓街,只保留了潭江邊的一段,其餘的都是擴建或仿造,規模明顯擴充,歐陸風情的房子也醒目了很多。但整個鎮已不是普通民眾的生活區了,而是十足十的對遊客開放的旅遊景區。拿着入場門劵走在鎮上,聞不到熟悉的煙火味,看到的都是仿製的民國招牌。如果在拍攝《三家巷》《廖仲愷》《讓子彈飛》《一代宗師》等影視作品,倒也能傳導出某種歷史情景,但我親身走在這現場實景中,嶄新的古董有軌車叮咚作響擦身而過,強大功率的喇叭蹦出震耳的歌聲混雜着空氣中的啤酒香味,卻無法找到那種歷史情懷,明顯感受到的是一種遊樂場的氛圍。當然,這只是我很個人的感受。畢竟,我當年曾見識過日常人煙的赤坎,期望能再次領略到文化保護下生氣勃勃的赤坎。但有點失落了。
對於歷史文化遺存,究竟是保持自然原生態,修舊如舊好呢,還是擴大規模,仿建新造,營造氣勢好呢?我很困惑。透過歷史鏡像,那種看相陳舊,那種痕跡斑駁,那種不完美卻又獨特的形態,不正是歷史的記憶,文化的印痕,歷史文化遺存的價值所在嗎?相比之下,我更喜歡自然狀態、原汁原味,看似不起眼,卻又獨一無二、意蘊豐富的碉樓。你說呢?
本文由看新聞網原創、編譯或首發,並保留版權。轉載必須保持文本完整,聲明文章出自看新聞網並包含原文標題及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