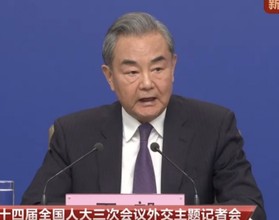一幢造型獨特的黑色洋樓佇立在基尤大街的交匯處,從馬路不同的角度望過去,那洋樓猶如一隻巨大的黑色蘑菇長在一片鋼筋水泥的叢林間。穿梭其間的有軌電車斯斯文文地行駛着,如忠誠而又老實本分的英國老僕始終堅守沉默敦厚的姿態,連電車司機仿佛也受了感染,絕不粗魯急躁地亂鳴笛,除非情不得已。
伊琳跳上一輛老式48路有軌電車穿越市區,電車一路行進在山體鑿開的路軌上,一面是綠植苔蘚的峭壁,一面是從高地流經河谷的溪流。二月的風還有些晚夏的燥熱,伊琳拉下老式電車的車窗,讓風吹進車廂,一縷陽光撒在她臉上泛起些許油光。
「世間有一種旅行,不是去往遠方,而是在通往一顆心的路上。伊琳,你要聽從你內心的聲音。」
「辛迪,你說的話怎麼和心理醫生一個調調。」伊琳撇撇嘴。
「怎麼樣,我也可以做你半個心理醫生吧,」辛迪笑言,「不過我的意見可是帶有個人色彩的,僅供參考喲!」
「你別說,心理醫生這活還真不好干,一個活體思想垃圾收集場,心理健康的人也要聽殘廢了!官方統計每五個澳洲人中就有一個人存在心理問題呢。」
「每五個中就有一個,這麼誇張,有這麼多嗎?」
「有呀,只是我們普通人諱疾忌醫不當回事,不良情緒持續超過兩周不能緩解,就算輕度抑鬱了!這可是排在癌症和心血管疾病之後的第三大疾病呢。所以澳洲政府非常重視,每年財政專項撥款用於防治心理疾病呢!」
伊琳又再次獲得了政府批准的心理健康計劃療程,每次前去心理諮詢診所的路途就像翻開一頁頁繪本,時而清新療愈,時而幽黑奇幻,通往那個她未知的內心世界,那片被她有意無意暗藏起來的布滿荊棘和重重迷霧的記憶森林。就像伊琳此刻坐在電車上想着和辛迪的對話,分不清自己置身都市還是誤入了森林。
心理診所等候室的牆上繪着一株綠色的蒲公英,它彎着纖細的長莖,微風把一朵朵蒲公英小傘吹向遠方,伊琳的思緒也隨着蒲公英飄向了遠方……
「我聽你姆媽說,你還想分你丈夫的財產!那些錢都是你賺的嗎?你太令我失望了!」 伊琳從中國移動銷戶回來,剛踏進大門便覺山雨欲來風滿樓,坐在紅木搖椅上的父親停止了悠閒地搖擺,臉色鐵青,周身散發着寒氣。
伊琳心裡頭一驚,她看向母親,母親手裡的縫紉針一偏戳到了自己的手指頭,連忙吸吮着滴血的手指不敢抬頭。看來母親又一次把她們母女之間的私房話出賣給父親了,這大抵這就是伊琳青春期始就不愛和母親說心裡話的緣由。
「爸,為什麼我不能分到財產,我是做了許多年家庭主婦,但家庭主婦對婚姻家庭的貢獻和賺錢的丈夫是同等的!婦女的合法權益是受法律保護的!」
「法律!那是法律偏袒了你們這些婦女兒童!」伊琳真搞不明白父親為什麼不幫着自己,反而胳膊肘往外拐。他這是幫理不幫親呢,還是僅僅出於對男權的維護。
怪不得丈夫唐會沖她叫囂:「你想離婚,我先問問你父親會不會答應吧!」果然他們才是一丘之貉心意相通。
「結婚當年也是你自己要結的,我們父母沒有干涉過你的自由,你現在又想要離婚了,是不是你翅膀長硬了!你讓我們的老臉往哪擱,我們沒有你這樣的女兒!」
「結婚自由,離婚也自由!」 伊琳全身都燃燒起猛火,每根毛髮上都閃着火星,她早忘了父親已八旬高齡,「你們光想着自己的面子,光看着我表面的風光,我為什麼要假裝活得幸福?活着就光為了面子嗎?活着就光為了物質嗎?我精神的痛苦難道就不是痛苦了嗎?」伊琳的手掌拍着紅木桌面「砰砰」作響,鐵一樣硬的木頭怎會疼,恐怕只有她的心比手更疼。父親沉默着。
「我去過寶林禪院進修,我去過基督教堂禮拜,我也去做心理輔導,我一直在調整自己的心態,我也在反思,否則我哪有勇氣今天坐在這裡面對你們!」伊琳幾度哽噎,母親抬起頭看她,眼裡滿是憐惜。
「是的,沒人能再折斷我的翅膀了,不是我的翅膀硬了,而是我現在有足夠的心理承受能力來忤逆所謂的權威了,我不是要來控訴討伐原生家庭的,我只是想讓你們知道,所有女性委曲求全的討好型人格都是專制的家庭和社會一手灌輸造就的。」伊琳眼中閃爍着淚光和不屈的光芒。
「重男輕女,男尊女卑,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中國的家庭和社會何時給過我們女性真正的尊重和保護!」
「沒有嗎,你的房間我們一直為你保留着,我和你爸歡迎你隨時回來住的。」母親忙不迭地辯解道,同樣生為女性她卻也在不知覺中把女兒當成了潑出去的水。
「那個住只是暫時的!如果我的人生失敗了,我在外面走投無路頭破血流了,你們仍然會毫無保留地接納我嗎?你們就是無法接受自己的女兒會是個失敗者!」伊琳淚崩。
「囡囡啊!你不要和你爸爸吵架了,他最近心臟不好,我們都是為了你好,為了你好呀。」母親出來打圓場。一句一切都是為了你好,多半是為了他們自己能心安吧。父親面色慘白捂着胸口癱坐在搖椅上頹然失神,伊琳驚慌得趕緊翻找着桌上的一堆藥瓶,找到一瓶麝香保心丸,擦乾眼淚倒了杯水給父親遞了過去。
「姐,你的行李整理好了嗎?我幫你搬上車。」伊琳的弟弟風風火火地衝進家門,看着屋裡緊張的氣氛不解道:「你們這是怎麼了?」
「沒什麼,你送你姐去飛機場,路上小心點。」母親把大衣紐扣多縫上幾針加固好,給伊琳披上,依依不捨道,「囡囡呀,你昨天突然買了機票說今天就要走,我這心裏面呀還真沒準備好呢,你出門在外自己當心身體,到了墨爾本就打電話來報個平安,不要讓你爸擔心,曉得伐。」
父親緩過勁來默默提起伊琳的一件行李尾隨跟着送出家門。
「疫情剛起,飛機場那麼亂,爸,您就別跟着去機場了,我送姐去飛機場就可以了!」
「好吧,一路上你自己保重,回去以後呀,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好好處理吧!」父親吃力地幫着把行李箱推進後車廂,喘着粗氣蓋上了後車蓋,他拍了拍伊琳的肩膀留下一句憋了良久的話,轉過身佝僂着背脊黯然離去。
「姐,你何必和父親當面起爭執呢,他那硬脾氣你受得了?你想做什麼事,自己去做就好了。」汽車緩緩發動開始前行,伊琳不知她的車窗後面,老父親已迴轉身站在保安室的屋檐下,露出一臉擔憂之色,目送着她的車遠去……
「丁零噹啷,」一串風鈴聲響起,診室的隔門從裡面推開,送走一位滿臉愁容的年輕人,心理醫生麥琪迎接伊琳進會診室。
「好帥的小伙子,這麼年輕,能有什麼煩惱呢?失戀了嗎?還是工作不順?」伊琳好奇心起,但心理醫生有保密之責。在國內我們肯定心裡一不痛快了就去找朋友訴苦,可朋友也不專業呀,只能傾聽你的煩惱而不能解決實質問題,而且也沒有義務一直當你的垃圾桶呀,時間一長估計連朋友都會受不了你的嘮叨,最終離你而去。
心理醫生麥琪是位眉眼彎彎的台灣妹子,花粉過敏季讓她的臉頰起了兩坨紅紅的疹子,讓人誤以為她剛去過西藏高原,伊琳只覺得她嬌小的身子裡藏着不可思議的力量,那麼多人的煩惱都壓在她的心頭。
麥琪拿出彩筆讓伊琳在白色卡紙上隨意畫個小房子,伊琳畫完停筆看着俯身過來看畫的麥琪,視線落在了麥琪烏黑的長髮上:
「穿過你的黑髮的我的手,照亮我灰暗雙眼的是你的眼……」,這伊琳的腦子裡竟然響起了台灣民謠,但願麥琪能照亮她灰暗的雙眼。
「人類自從創造了語言便開始無法真實的表達了,諾言、謊言、流言讓人們的心與心彼此遠隔,無法再彼此貼近。不如讓繪畫這無聲的語言來揭秘你的內心世界吧。」
看着伊琳畫的網格狀的屋頂瓦片,麥琪坐直身子手指靈活地敲擊着筆記本電腦記錄着:「你對自己的父母懷着深深的愧疚之情!」
伊琳心頭一怔:這也看得出來!
中國的孝道講究的是父母老了,可以坐享兒女的福。也許伊琳潛意識裡始終覺得她沒成長為值得父母驕傲的孩子,也許伊琳覺得自己顛沛流離的人生讓父母操心了,也許伊琳覺得自己對父母除了一顆赤心可獻其他寥寥。
原生家庭對每個人的成長都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並終將使你拼盡一生去抹除那些印記。幸福的人用童年去治癒一生,不幸的用一生去治癒童年。伊琳不再需要諾言,不再相信謊言,也不再介意流言,她只要做回她自己。滄海終有一天會變成桑田,冰冷的世界終有一天會改變。
伊琳獨自一人又回到了墨爾本,一次次地歸去來兮,青春將蕪,一次次地歸去來兮,老友將無,他鄉已然變成了故鄉,故鄉卻漸漸成為了那個無所留戀的遠方。
南半球的天空還是那般湛藍,朵朵白雲似觸手可及。一隊大雁「嘎嘎」地低空鳴叫着飛向溫暖的棲息地準備過冬,伊琳抬頭看去,那領頭的大雁歪了一下脖子似在向她致意,它的腳上似飄蕩着她的紅色髮帶,許是春天那隻受傷掉隊的大雁吧。伊琳不禁跟着天上的雁群跑了起來,「嗨,嗨,雁仔,是你嗎?你好呀!」
伊琳揮舞着手中的黃絲巾,目送着雁隊飛向遠方。
「伊琳,你在幹什麼?看你跑得這樣氣喘吁吁的。」
「噢,辛迪你相信嗎?相信嗎?我竟然……我竟然看見那隻春天落在我後院裡的受傷大雁了,它們剛飛過去,它現在已經……已經做了領頭的大雁了!」伊琳氣喘吁吁興奮得像在說自家得獎的孩子。
「你不會看錯了吧。」
「不會的,不會的,它剛才還對我鳴叫打招呼了呢,它腿上還有我當時給它包紮用的紅髮帶,我可是把我從國內帶來的一支金黴素眼藥膏全給它敷上去了呢。」
「是嗎,還有這等神奇的事!」辛迪一臉的不可置信,「說正事,我來是想請你明天去我香煙店,我明天轉讓店鋪要見對方買家和交接律師簽合約,你幫我來一起把把關吧。」
「好好,沒問題,提前恭喜你順利「畢業」,明天你可要請客吃飯哦!」伊琳敲起竹槓來。
翌日,秋高氣爽,辛迪開車接上伊琳就來到了位於圖拉克的香煙店。時間還早,兩人尋了家咖啡店一起坐在戶外遮陽傘下吃頓BRUNCH早午餐。伊琳喝了口拿鐵咖啡,奶泡上的愛心花紋瞬間化了開來,「辛迪,你什麼時候去意大利接你大女兒來墨爾本呀?」
「變更撫養權的官司沒那麼好打,估計一時半會兒還解決不了。」辛迪手中的餐刀把水波蛋切開,金黃的蛋液流淌在鋪了一層煎蘑菇的培根土司上,「你怎麼樣,分居到現在還沒下決心辦離婚手續嗎?」辛迪插起一小塊麵包和沙拉沾着蛋液,送進口中細細咀嚼着。
「都說長痛不如短痛,可我自己要過的始終是心裡那些關,我真想把自己的心剖開來看看清楚呀。」 伊琳手起刀落水波蛋被一切兩半,金黃的蛋液瞬間流淌下來,把一坨紅色的甜菜根泥圍成了一個紅太陽。「聽說芭芭拉去印度了,她去追尋一名高深的瑜伽大師薩古魯,去他的ISHA 瑜伽中心參加身心靈訓練營了,有機會我也想去看看呢。」
「是嗎,她乳房沒事了吧,現在搞靈修項目到處都很吃香呢!也不免魚龍混雜,希望她找的那位大師靠譜些。」
「哎,她沒事,虛驚一場!本來醫院就事先申明過:通知你複查不代表你就被確證得癌了,人呢都是被自己嚇死的!也都是被自己煩惱死的!做做瑜伽冥想或許對她有用。」
兩人就餐完畢回到香煙店後庭里坐等買家和律師到來。門鈴「叮咚」一響,沒想到推門而入的竟是高大帥氣的意大利帥哥馬修。「你怎麼和馬修還有聯繫,今天還把馬修給請來了?」伊琳大感意外,壓低聲音問道。
「噢,上次在意大利街吃披薩你還記得嗎?你上洗手間時,我和馬修互相留了聯繫電話。馬修中文英文都不錯,我讓他來幫忙看看英文合約把把關。」辛迪有點心虛道。
「那你還把我叫來當電燈泡呀!」伊琳故意嗔怪到。
「嗨,是伊琳吧,好久不見,你看起來精神不錯呀!」
「馬修,你真是好記性呀!」
「誰能忘了美女呢!」馬修的眼睛像蜜蜂一直盯着辛迪這朵花,伊琳看着馬修和辛迪曖昧的表情,抿着嘴偷笑看破不說破。
「叮咚」 門鈴聲又響,這次應該是煙店的下家來了吧。伊琳又伸頭去看店鋪大門。不想卻見黃景瑜帶着金絲邊眼睛提着黑色公文包跟在了買家的後面,伊琳不知怎地竟然一時想躲,已經來不及了,這巴掌大的小店往哪裡躲,華人的圈子可真是小呀!
「伊琳,好巧在這裡碰到你啦!」黃景瑜有些喜形於色,「你是不是把我給拉黑啦,我都沒法聯繫你了。」
「好,好巧,我,我……」伊琳承認也不是,不承認也不是。
「一會兒等我工作辦完,我們一起去喝杯咖啡,等我別走!」黃景瑜吩咐了伊琳兩句,趕緊和辛迪與馬修握手。這交接律師和清點公司都是買家負責找來的,估計辛迪也不知道來的律師會是黃景瑜。
人都到齊了,看着買賣雙方交涉着,沒伊琳什麼事,她推開了通往後院的小門,後院裡有一棵粗壯的銀杏樹,金黃的落葉鋪滿整個小院,兩根粗礪的麻繩從粗壯的枝椏上垂吊下來,綁着一塊舊木板做成了一架鞦韆。伊琳踩着沙沙的落葉,坐到了鞦韆上慢慢晃蕩起來,腳下的黃葉隨着她飄動的白色裙裾在底下四處翻飛着。一會兒怎麼面對黃景瑜呢?她是把黃景瑜的聯繫方式都拉黑了,連她自己都不清楚到底是為了什麼。她掏出手機,把黃景瑜的電話暫時移出黑名單吧。她翻看着手機新聞百無聊賴,忽聽背後有沙沙的腳步聲,她調轉鞦韆的方向,見是黃景瑜健步走了過來,她本想瀟灑地一躍而下,沒料到卻失去了重心,一個出溜從鞦韆的後方倒栽蔥摔了下去,只聽「撲通」一聲,伊琳摔了個四腳朝天,一篷落葉飛起擋住了她的春光乍泄。
「怎麼可以在黃景瑜面前這麼丟臉呢!」伊琳快速整理着裙擺想要爬起身來。
黃景瑜已跑到鞦韆下,「伊琳你沒事吧!」他拽着伊琳的胳膊想要把她拉起來。
「丟死人了!竟然在黃景瑜面前這樣走光!摔得這樣狼狽!」伊琳惱着借力拉着黃景瑜的胳膊只想站起來,卻被自己的大裙擺給絆住了,拉着黃景瑜又一次摔倒在了落葉之上。落葉漫天翻飛,黃景瑜健碩的身子重重地壓在了伊琳的身上,看着黃景瑜的唇幾乎要貼到自己的唇上,伊琳忽地想起了自己做的春夢,臉騰得一下升起一片更深的紅暈。
「黃律師,黃律師你在哪裡?」辛迪的聲音在後院門口想起,「哎呀,你們兩個怎麼躺在地上抱在一起呀!」
伊琳趕緊推推愣在她身上的黃景瑜,「你快起開呀!你好重壓死我了!」
黃景瑜爬起身,順勢也把伊琳拉了起來,幫她撣去頭髮上的枯葉,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西裝,關切道:「你沒受傷吧?」
「沒沒沒,你快去辦正事吧。」伊琳紅着臉低頭整理着裙子。
「黃律師,貨物清點完了,可以交接簽支票了。」辛迪把黃景瑜喚進屋內,走過來揶揄地看着滿臉通紅的伊琳,「伊琳,瞧你臉紅的像個猴屁股似的,你們倆這是慾火焚身,在我後院裡席地為床呢!」
「去去去,就你沒正經,我們就是摔了一跤而已嘛!都怪你那破鞦韆!」伊琳回頭瞪了眼鞦韆架,她沒人好怪罪,只好怪罪那塊破木頭嘍!
作者:簡西
本文由看新聞網轉載發布,僅代表原作者或原平台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立場。 看新聞網僅提供信息發布平台,文章或有適當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