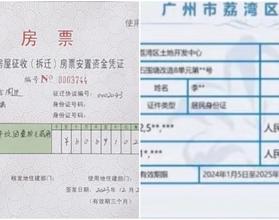小鎮做題家是近年來的熱議話題,而作為他們階層躍遷故事的背景,是那些一直沒有機會離開村鎮的人。他們受教育程度不高,留守村鎮,隔絕於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進程。
家庭資源有限,城市生存經驗不足,這些沒機會離開小鎮的人,將進城視為一種「妄念」。
小鎮修理鋪,日入三元
晚上約莫5、6點光景,王學勤和妻子楊鳳珍開飯了。桌上擺着臨街店鋪賣的熟牛肉、熗炒過的自家種的青菜,還有一瓶太原高粱酒。王學勤邊喝酒邊吃菜,楊鳳珍說話間,則不停對丈夫翻着白眼。
年前,兩人鬧了點兒矛盾,王學勤開一家家電修理鋪,這天他不在,有人來取修好的電視機,楊鳳珍作主收了三十元。王學勤回來後,立馬發了脾氣,他認為那三十塊錢收「貴了」。而楊鳳珍也絲毫不讓理。「光圖名聲能圖來錢?」提及此事,二人不免又是一番拌嘴。
爭執間,一位老人來修電飯鍋。開關壞了,王學勤為他換了副新的,連零件帶修理費,只收了三元錢。按楊鳳珍的說法,這就是開年後的第一份收入,聽起來不免帶着點兒窮酸。
這是2020年春節,正月大年初八,王學勤和楊鳳珍夫婦守在修理店內,就這樣度過了一個春節。
王學勤夫婦在鎮上開修理鋪已30餘年。鋪子就在自家自建房內,毋需房租。一年四季,王學勤大概都戴着墨鏡,坐在一張舊木桌前,進行電路板焊接,楊鳳珍負責招呼顧客。2014年她患上中風,落下半身不遂的毛病。身體狀態好些時,店裡一有人來,她仍會倚着門框走出,笑着招呼,要給人倒水、同他們聊天。
楊鳳珍患病前,王學勤夫婦除春節或特殊節日,幾乎都要開店、守着店面做生意。大兒子王大雷在鎮子幾公外的鄉村開家電修理鋪,二兒子王小雷在鎮上開摩托車修理鋪。顧客大都是四里八鄉的熟人,店鋪開在自家的房子,吃的是自家土地里產的糧食和菜園裡的菜,肉去街上買,生活成本低,雖一年四季守在店裡,但有錢賺,日子還算自在。
鎮子位於山西晉南,這裡丘陵和坡梁起伏,在此地靠種地掙不上錢。鎮子十多公里外的東山,蘊藏有豐富的鐵礦,上世紀90年代,一座鐵礦廠矗立於此,晝夜不息地閃爍着火光,輸送礦產資源的交通幹道與鎮子主街交叉,構成一條繁榮的商業地帶。
王學勤夫婦是最早把握這波經濟紅利,從村里移居到鎮上的人家。王學勤的父輩是農民,高考落榜後,王學勤開始自學家電維修技術,初來鎮上幹個體戶時,只能住在租借的馬房中,積攢財富後,才在鎮上置地建房、娶妻生子。
那時,繁榮的小鎮吸引來一波流入人口。有王學勤這樣來自附近村子的農民,憑手藝開店,諸如小飯店,理髮店、蔬果店、車輛修理鋪等等。也有來自四川、湖南的外省人被礦場吸引,前來賣力氣。
2005年後,礦場陸續關停,鎮子的發展速度放緩。2012年前後,縣城房地產生意紅火起來,鎮子迎來了人口外流時期。鎮,作為城市與縣城的中間態,曾被許多從鄉下渴望到縣城的人們視為中轉站。鎮子衰落,年輕一代紛紛選擇離開,去往經濟更發達的縣城,或去省城務工,匯入浩浩蕩蕩的城市打工潮之中。
但那時,王學勤和兩個兒子不想進城,也不怎麼想出遠門。他們的生存圍繞本地的社會關係和人情展開,一家人也留戀故土。
王家第二代中,王大雷夫妻是最早選擇出走小鎮的人。2014年前後,他們苦於鄉里的生意冷清,率先關掉修理鋪,分別進入省城的家電城和電子廠。兩年後,二兒子王小雷關掉鋪子,為兒女讀書,也搬往縣城。
留守此地的王學勤,和鎮上沒落的郵局、家具廠、服裝店以及坑坑窪窪的炮彈路一起,像是兀自構成守護舊世界的結界。
2015年,楊鳳珍一陣陣犯頭暈,她身形高大,自認為身強體壯,起初並未在意,直到一次,上廁所時差點兒暈倒,王學勤帶她去縣醫院檢查,人已患上腦梗。不久,楊鳳珍爆發肢體障礙,住院治療了一陣,因錯過最佳治療時機,落下半身不遂的毛病。縣醫院醫生無奈告知,只能靠藥物和鍛煉儘量維持現狀。
王學勤一面看顧維修鋪的生意,還要照顧生活不能自理的妻子、大兒子留守在家的兩個孩子。他不堪重負。為給妻子看病,讓她的日常生活可以自理,王學勤沒少求醫問藥,從大醫院到小診所,從游醫偏方到神漢假藥,只要聽說有用,他們都願意嘗試。年近60歲,為外出看病,夫妻倆才偶爾會閉店,離開小鎮。
出走
作為小生意人,王學勤幾乎一輩子未離開縣域範圍。本地人信奉紮根守業,王學勤也幾乎將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獻給小鎮和家電修理鋪。
王學勤的家鄉在鎮子十幾公里外的鄉下。他頗有些少年「天才」,年幼時在村子裡拆卸組裝家中的半導體收音機、村里廣播喇叭,甚至能靠修半導體錄音機掙上工分。70年代末,王學勤高考落榜,父親一捲鋪蓋,將他送到鎮上租借的一間閒置馬房,王學勤干起了「個體戶」。
8、90年代,王學勤抓住縣城購買電視機、收音機等電器的熱潮,靠看《無線電》雜誌等自學,成為鎮上最早的家電修理師傅之一。那時,鎮上人對他最深的印象,便是他騎一輛二手摩托車,紅色漆皮,超大油缸,發動機一開動,便發出破鑼聲響。行駛起來,更會拖出一條濃黑的尾煙。騎着這輛摩托車,王學勤也因此成為鎮上最早的萬元戶之一。
隨着業務擴展,王學勤的修理鋪從馬房搬遷到了鎮上最熱鬧的廟場,賺到了錢,王學勤渴望在鎮上安居樂業,他買下平房所在的地基,房子先起一層,又加蓋一層,樓上樓下七八間,在鎮上也稱得上「豪宅」。
當時,縣供電局甚至來挖「人才」,想安排他入編制,但王學勤覺得幹個體也更自由,拒絕了這份「官差」。
或許是自學技術謀生給的底氣,王學勤對兒子的學習不算重視, 「讀個九年義務教育就行」。大兒子王大雷從小愛跟父親搗鼓家電,初中畢業後,王學勤教給他修理家電的技術。後來,將上門維修這部分工作分配給王大雷。2003年,王大雷結婚後,在距離鎮子3公里的D鄉開設維修鋪,專注於「大鍋」(衛星接收器)安裝業務,父子二人修完大半個縣城的家電,完全不愁生意,他們也成為親戚中最闊綽的人。
小兒子王小雷15、6歲時,去一家摩托維修鋪成為學徒。學成後,王學勤花費6萬元,在鎮子街道購置一塊土地,為王小雷建造自建房,並開設摩托維修店鋪,王小雷也成家並自立門戶。
同年,王大雷的女兒和王小雷的兒子出生。兒孫滿堂的王學勤迎來人生最高光的時刻。那幾年每逢年節,王學勤家中格外歡鬧,連鞭炮和禮花都要放得比別家要多,要響。
一派繁榮背後,也有暗面。2005年後,私挖亂采導致的事故頻出,加之生態政策的收緊,大小礦場逐步關停,在鎮上繁忙了十餘年的煉鐵廠火光冷卻。這座煉鐵廠一度是小鎮經濟繁榮的象徵。在礦場打工的本地人在其中賺到了錢,成為鎮上首先富起來的一批,前來打工的四川人、湖南人等外省人,都帶動和促進了鎮上的經濟和消費。
礦場關停,本地和外地人都走了一批。王學勤那時並為想到,經濟支柱的逝去,成為鎮子營商環境慢慢衰落的起點。
直到2012年前後,親戚間開始有人在縣城或鎮上買房、讀書,向縣城流動。但王學勤仍沒有這方面的心思,兩個兒子也「戀家」。他們喜歡吃本地的麵食,住慣了寬敞的自建房,也走慣了泥土路。對於王學勤來說,鄉土宛如身上的肋骨,抽掉後會感到切膚之痛。
不斷更新的技術,也衝擊着王家的生意。2012年,寬帶網絡和機頂盒在鎮上逐漸普及,傳統的「大鍋」逐漸從各家各戶的屋頂上消失,數字電視服務成為潮流。王學勤和王大雷的業務量一落千丈。為維持生計,王大雷在家電修理鋪拓展了一塊區域,開始兼營五金業務,效果並不理想。當時,有人跟他說了博彩這一賺錢門道。隨後,他鋌而走險,在店裡順帶經營起黑彩網站的代理生意,能擴大收入,但也比不過鎮上經濟好時、家電維修鋪的鼎盛期。
沒過兩年,這一非法業務就被打擊和取締。2014年,王大雷無奈關閉了維修鋪,他遠赴省城謀取機會,在一家大型家電商城擔任維修諮詢師,起初月薪3000元。他的妻子李玫隨後也追隨他前往省城,進入了省城的富士康電子工廠工作。
他們將在鎮上開鋪子時的經濟頭腦延續到省城。李玫在工廠工作2年,得了腮腺炎,厭倦電子廠的工作環境後,她退出工廠,做起產品直銷,王大雷也被妻子帶入了這一行。剛開始,夫妻二人順利賺到了些錢,手頭寬綽,消費也升級了,先是在縣城買了地段最好的期房,後來又換了新車。
弟弟王小雷的進城務工之旅則相當曲折。大哥的家電修理鋪關停後,他的摩托車修理鋪在鎮上勉力維持了2年。生意冷清,時間久了,他心氣受挫,妻子看店時,他流連於附近的麻將桌。挨到2017年前後,鎮上撤學並校,先是中學撤銷,後是小學生源外流,教學質量滑坡。儘管不願離開鎮上的家,為了孩子讀書,王小雷和妻子還是決定帶着孩子前往縣城租房陪讀,一面打打零工以維持生計。
他先是由嫂子介紹進入富士康,在鎮上開店自由散漫慣了,他不適應工廠里嚴苛封閉的工作環境,不久便離職而去。2017年秋,他由一位朋友介紹來到北京找工作,結果誤入傳銷組織,最終由一位在城市工作的表親將他接回。
自此,王小雷對城市心生排斥。回鄉後,他選擇留在家鄉開金杯貨車,接的活兒也圍繞家所在的區域展開,不過,這樣跑車能賺到的錢不多。
而這時,王學勤在鎮上打拼的根基、經驗與智慧,已無法再助力兩個兒子在城市的生活。他同時自身難保。妻子患病後,家中大多積蓄都花在看病上。2019年前後,急於為妻子看病的他,曾花5千元買下據說有神效的「西藏靈芝」,楊鳳珍服藥後卻出現高血壓、便秘等症狀,停用、送檢後,才知道是假的。他又受「醫托」鼓動,衝動買下去山東濱州的聯程車票,打算去一家號稱用「幹細胞療法」治療、吹噓得天花亂墜的民營醫療機構治療。
幸好在出發前夕,在縣城的小兒子王小雷及時發現並阻攔。為此事,父子倆一度陷入冷戰。被傳銷欺騙過的王小雷認為「醫托」不靠譜,王學勤則指責兒子怕出醫療費用。「醫托」的騙子身份被揭露,山東之行不了了之。王學勤後怕,如果再去一次,怕是家底兒要空掉了。
這次經歷,讓王學勤也生了對城市「魔窟」般的想象。他性格本就沉默,不愛說話,那之後,王學勤鮮少再提去城裡帶妻子看病的事兒,有時楊鳳珍向過路人打聽哪個地方的醫院好,王學勤只擺一擺手,臉上是聽天由命的平靜,「別想了」。

活成鎮上基建服務的一部分
如今,王學勤還在努力維持着敗落的生意。他有心研究電腦和手機的維修業務,但到底年齡大了,腦力和精力跟不上探索。
而他的修理鋪仍在服務着鎮上的人們。來修東西的多是上歲數的老人。老人們過慣節儉日子,送來的老物件拆調一番,換個不值錢的小零件,又能支撐個一年半載。一次,一台修好的舊電視長達一個月沒人來取,連王學勤都忘了是誰,回頭看到戴孝的人來,猛然記起那台舊電視。對方面容慘澹,嘆一口氣,「取不取也沒多大意思,上次趕集之後的第二天,人沒的。」這台電視到底沒被拿走,王學勤硬塞了對方二十塊,等於收個舊東西。
店裡留有太多舊家電和物件,因「人情」一概堆積在店鋪的角落。平生第一次,王學勤把油漆塗寫的「家電維修」四個字明示在月亮門的牆面上,以此說明他還在幹這一行。
固守鎮子的兩代人,似乎仍在等待轉機。2022年,王學勤從他人口中得知,兒子和兒媳大打出手,據說要離婚。他詢問後才得知,2021年,李玫搞直銷過程中聽信他人,誤入網絡「殺豬盤」,還拉了不少親戚朋友下水,每家都出借了數千到數萬元不等,結果對方捲款跑路,夫妻倆最終背上三四十萬的外債。但得知後,王學勤無奈地說:「管不了了,自己解決吧。」
王小雷在大城市遇挫後,2017年後,他大多數時間,像候鳥般往返於縣城和鄉村,沒事兒時,他還會回到村裡的老家住上一陣。唯有在鄉土,王小雷才覺得親切和安全。2020年,他加入村委會,當起小組長,為母親楊鳳珍辦理二級殘疾證,爭取到每月發放的50元生活補貼。
王小雷育有兩個兒子,如今,一個已上大學,一個在上小學,都處在「花錢」階段。他和妻子在縣城租房住,妻子在快遞點打包,王小雷則靠開小貨車賺點兒小錢。
他挖空思想想賺錢。但沒落的山鄉小鎮,如若不外出打工,實在出路難覓。2023年,王小雷去了趟呂梁的礦場,但險些遭遇礦難。這趟回來後,迷茫的王小雷多半時間選擇了在縣城「躺平」。沒有拉貨生意的日子,王小雷保留着搓麻將的愛好,贏了請客吃飯,輸了則蹭吃蹭喝,狀態看似瀟灑,實則要靠拆藉以及「擼口子(借網貸)」舉債來維持。
眼見着兒子未能出人頭地,現在的王學勤,只將希望寄托在孫子輩上,總想着哪天哪一個能出頭,至於「能出頭」究竟意味着什麼,王學勤也說不清。
王學勤的家電修理鋪仍在鎮上矗立,但偏於一隅,像個垂垂老者,仿佛被時光所遺忘,再難找到結實的存在感,而承受着「摩托」風濕腿病的他,也同修理鋪一道,正彎曲地步入他的暮年。
窘境同樣懸掛在楊鳳珍臉上。她如今靠着服藥和鍛煉,拖着病體,需要一點一滴算計過日子。一件拆封的快遞衣服,說是拼團所購,試穿了,質量太差,樣子也和網絡圖片不對版,要拿去退。她從不去鎮上新市場的實體店買,在鎮上的人看來,除了逢集或節日時,「那地方賣東西的比買東西的多。」
過去十年家中從小康陷入困頓的生活,她無法全然理解。有時,楊鳳珍會想象當初丈夫進了供電局去了縣城,今天的日子是否會不一樣。 「發祥(王學勤的朋友)在供電局退休,現在一個月三四千。」她慨嘆自己「沒那個吃財政的命」。
提及鎮上其他小店的生意,除了一家老字號的牛肉館還很紅火,王學勤對別的營生只有搖頭嘆息。不過,之前王學勤去買牛肉時店裡要送上一塊肉的習慣,店家已經悄然更改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真實故事計劃
本文由看新聞網轉載發布,僅代表原作者或原平台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立場。 看新聞網僅提供信息發布平台,文章或有適當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