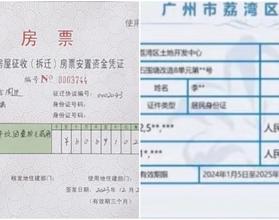過夜
深冬的上海,夜裡氣溫逼近零度。27歲的王林森被凍醒,站起來踱步暖和下身子。他到得太遲,沒搶到有桌子的好位子,在長椅上睡睡醒醒一夜。伴隨他的,還有玻璃牆上那句「住宅里沒有書,猶如房間沒有窗戶」。
這是一家24小時營業的圖書館,和平書院,位於虹口區和平公園五號門。第二天一早要在市區面試,王林森不捨得花錢住賓館,就在網上搜索免費過夜的地方,找到這裡。上一次這樣過夜,還是在北京坐徹夜的環線公交——沒趕上地鐵末班車。終點站下車,刷卡再坐下一趟,就這麼一直坐到早上五點,等頭班地鐵回家。

元旦前兩天,他來到上海,想在春節前找到一份工作,趁假期幹活多掙點加班費。面試的公司離和平書院不遠。他到圖書館時已經晚上十點,一樓餐廳閉餐了,免費閱讀區的十來張圓桌已有「領主」,尤其是靠牆的一排,因為方便充電早早就被占據。
多是備考的年輕人和加班的白領,也有王林森這樣拎着大旅行包的,把包立起來當抱枕,支着下巴睡。角落的位置通常被常居客占領,他們很容易辨認——穿拖鞋,襪子髒髒的,帶着背包、編織袋,或乾脆就是個透明塑料袋,裝着換洗衣物,可能還有剩下的半盒飯菜,散出味道。他們自覺地不坐到用餐區,即使打烊後那裡已經變成免費區域。
凌晨兩點過後,大部分人泛起困意,以各種姿勢睡去。有桌子能趴着睡的位置是有限的,去晚了只能像王林森一樣坐着睡。一晚上至少要醒兩三次,可能是打鼾被喊醒,也可能是睡麻了身子,乾脆起來上個廁所,回來換條胳膊枕着繼續睡。
王林森在圖書館過夜的第三天,晚上八點左右到的,占到了包皮面的椅子座位,桌子也大些,還背靠牆,「想怎麼趴就怎麼趴」。他新加了一件棉衣,度過了最舒坦的一晚。
那是今年元旦,他遇到了常居客鄢悅。鄢悅笑起來顴骨隆起,穿12塊錢的白色橡膠拖鞋,漫步在圖書館,就像在自己家客廳。
白天在「書房」溜達——在圖書區看書,累了就到外面公園涼亭里躺一會兒,那是白天的「臥室」兼「餐廳」。圖書館二樓的沙發區不能躺,會有工作人員過來提醒,但躺下是必要的,鄢悅見過一個大哥,趴着睡了幾個月腳腫得發紫,不得不去租房住。陽光好的午後,鄢悅喜歡在涼亭和圖書館之間的草坪上,曬會兒太陽。
每天十幾塊團購一餐飯,比外賣便宜。洗漱在公廁,洗腳就着洗拖把的池子。冬天不太出汗,每兩周到健身房去洗次澡。周卡20塊,用優惠券還能便宜幾塊,沒有浴巾,就用吹風機吹乾身體。
他的行李只有一個充電寶和一個像導遊常背的黑色腰包,包里放着牙籤,數據線、黑色襪子。沒有換洗衣物,就那麼一身,穿髒了就扔。入冬後扛不住,五十塊網購了一件裡面帶絨的防風衣。鄢悅介紹經驗,一定買那種戶外的面料,「髒了擦一下就乾淨了」。
偶爾到肯德基或者麥當勞蹭網,圖書館的Wi-Fi需要辦讀者卡。他去問過,除了押金還要填家庭住址等一堆個人信息,他放棄了。
鄢悅去年九月中旬來的上海,十三四個小時慢火車晃過來,票價177.5元。在上海,去哪裡都靠走,連公交都不坐。到圖書館的路上,路過袁記水餃店,他用團購券買了一份6塊7毛錢的拌麵。
300塊錢半個月花完了。後來他借了五六千塊網貸,還在手機軟件上做返現任務賺零花錢。現在每天的飯錢減少到十幾元,有時在拼多多買壓縮餅乾吃一天,「躺着不動,減少消化。」鄢悅總結出最新經驗。
四個月在圖書館過夜的日子,他摸索出一套方法論:找幾本書墊在桌上,這樣就不會被桌子冰到;兩個手掌上下一疊,腦門扣下去,一晚都不用換姿勢。憑着這套生存法則,鄢悅成了王林森眼裡的「三和大神」——以一種非常低消耗的姿態生存,活在困頓生活里的人。
保安對躺沙發不那麼嚴格管理的夜晚,鄢悅就半仰在沙發靠背上,臉衝着屋頂,和王林森講自己過去35年的經歷。王林森開始擔心,如果再找不到一份穩定的工作,自己也會和他一樣,滯留在這裡。王林森心裡盤算着,第二天的面試如果通過,就不用再回來這個地方。
過客
住進圖書館,鄢悅以為找到了同類,盤算着拉一個省錢互助群,最好能結成搭子,這是他來和平書院最大的動力。
觀察了幾天,他發現五六個常居客。有一位中年人,隔幾天來一次,白天固定的時間出門,他猜測對方是打零工的。一個00後女孩也每晚來,有天坐着突然失聲哭出來,發覺引來目光,趕緊低頭趴到桌上。還一位高個子男士,身體也壯,看着不好惹的樣子,但聲音溫柔,會主動幫別人撿掉落的東西,有人同桌睡覺,會把胳膊縮一縮。
他嘗試跟這幾位挑起話題,問吃過飯沒,對方都以「吃過了」或「沒吃過」三個字中斷對話。後來他改變話術,琢磨出最容易拉進距離的話題——「4塊錢一頓吃不吃?」——把手機上的拼單展示出來。也沒能打開話題,那位00後女生第二天沒再來,鄢悅猜是被自己嚇跑了。

去年十二月,他遇到做二次元虛擬主播的一個小伙,身上汗味很大。他猶豫要不要分享健身房洗澡的路子,又擔心傷了對方自尊。失敗的社交嘗試讓他發現,大家並不需要抱團也不要幫助。
倒是兩個四十多歲的男人主動跟他攀談。一個是學哲學思修的,想要靠教育賺錢。另一個在圖書館用傳統茶道方式泡茶,聊佛學,請人到自己的茶室飲茶,付不付費隨意。後來倆人合作創業,自稱會長和副會長,還吸納了一個年輕人,具體做什麼不清楚。
「好像跟茶有關」,鄢悅說,「會長」第一回來的時候,急着要充電,找他借充電寶,另一個句句不離錢。
這裡不缺做夢賺錢的人。英語補習教師于楓今年40歲,帶着一副眼鏡,喜歡帶兩大一小杯子,放在圖書的隔斷上沖泡速溶咖啡,啜上幾口,開始暢想未來——用補習掙到的錢投到一支好的股票里,「過個十年翻個3倍」。
三年前,他在股市賠了錢,也辭掉留學申請中介的工作,開始一門心思搞補習培訓班。現在計劃寒假招一批學生,在他的描述中,這種補習來錢很快,一個家長一次性支付七八萬,「100個學生就是700萬」。
于楓目前招攬到的學生有7個,天氣暖和的季節,他和陌生人合租住八人間,自從羽絨被在共享單車筐里丟了之後,就開始來圖書館過冬。離100個學生的目標還差得遠,他認為不重要,「重要的是結識中產圈層的家長,一起做投資,在股市捲土重來。」
的確有很多家長帶孩子來這裡看書、寫作業,尤其是周末。除此之外來這裡最多的,就是為工作發愁的年輕人。早上八點,圖書館門口就擠滿占座兒的隊伍,二樓的幾張寬大桌子是首選目標。午飯時,他們會把東西留在座位上。
25歲的投行從業者鄒琪點了一份肉醬意面,49元。上班快一年,周末加班是常態,鄒琪不想獨自窩在家,更願意到圖書館、咖啡廳這些有人氣的地方,她喜歡被陌生人陪伴的感覺。去年聖誕夜,她也是這麼帶着工作離開辦公室,找了一家餐廳坐下來。
英國法學碩士畢業回國,律所的工資只能從三千開始,她轉而進入金融業,趕上整體降薪,工資一萬出頭,相比往年的新人少了大幾千。
父母補貼她租房,每月四千,然而並不能撫慰她工作上的受挫。因為數據弄錯被客戶當面諷刺,又被領導臭罵一頓,父母常在夜裡收到她的哭訴。她在上海有不少同學,親密的一個月才能見上一回,大部分時候是兩點一線。
租房的時候,鄒琪特意選了一間帶陽台的,視野寬闊,能看到陸家嘴的高樓。她還買了一套卡通廚具,收在櫥櫃裡一直沒用。1月5日那天,她待到晚上十點才離開。
來自河南的張劍稍早幾天聖誕夜來到圖書館。他做過電銷和房產經紀,但性子內向,講話有些吞吞吐吐,常常業務沒做成,還被客戶要求換人對接。
雙胞胎哥哥在武漢工地上做工程造價,一月到手萬把塊錢。父母在老家是茶農,前些年給哥倆在鄭州買了房子。不過他聽父親說,今年茶葉銷量大跌,現在還有500多斤貨壓在家裡。
他不願主動聯繫哥哥,似乎大學畢業後,他們的軌跡就走向兩個方向。2022年,他從一家二本院校軟件工程專業畢業,但沒有實習經驗,找工作時屢屢被卡在門外。要好的幾個同學都在互聯網行業,他也想過,只是沒辦法從實習生做起,就算脫產幾個月自學相關技術,還是會卡在缺乏項目經驗。「錯失實習機會」,他形容當初的自己。
在上海找了幾天工作,約面試的都是網約車、外賣這類服務崗,他又開始投遞銷售崗。
過生活
這裡像個人生中轉站,大部分過夜者,住幾天找到工作就走,也有打零工的在空檔期斷斷續續回來。
鄢悅是那個被留下的人,沉浸在書海里雕琢思想。四個月里,他看了十來本書,最近看的是《非暴力溝通》《逍遙人生:莊子傳》和《健全的社會》。有時狀態好,一天就看完一本,有時一本書怎麼也看不進去。他清楚這不是長久之計,「先混着,沒錢了再說」。
剛來上海的時候,他試着找過工作,發出去的信息一大半都沒有回音。也想過干體力活,七八千一個月做老年護工,他問對方,「是不是要對老人卑躬屈膝?」問寵物救助站,兩千一個月,對方猶豫他沒有經驗。
找工作並不上心,鄢悅承認,或許是還沒到絕境。「我是每次身無分文之後,馬上就找到事做了。我知道解決方法,但我就是不去做,這才是問題所在。就像我的傲慢一樣。」
父母從小離異,後來父親有了新家,他也有了妹妹,小他一輪。在鄢悅印象里,繼母待他不錯,但父親搬入新房後,他就很少回廣西老家,開始了「沒有下一步規劃」的生活。
七八年前在北京的時候,他在昌平區合租到十平米的一個單間,月付600塊,每天出去吃飯、到處閒逛。錢很快就花光了,父親拒絕給錢,他只好找了份保安工作,帶着狗巡邏。
在那之前,他在威海做過七八份工作,長的幾個月,短則幾天。中介不願再介紹工作給他,他給對方發信息說想寫個小說。最拮据的時候他每天喝白粥,後來聞到粥味就犯噁心,還是吃下去。
疫情期間他又去了威海,窩在那裡,寫了部二十多萬字「自嗨的」小說,關於父親和女兒。小說主角是按自己的形象描摹的,女兒是他在現實中無法達成的心愿。他發到網上,原本期待一些銳評,點醒自己的思維盲區,結果只有三十幾個點擊量,一條評論都沒有。
和平書院本來只是個臨時居住點,住着住着,鄢悅就習慣了。網上借了五六千元,分期13個月還,還剩下兩千多。他承認自己算是啃老,「一直給的話為啥要干(工作)?」
在和平書院,他試過在二樓沙發躺幾分鐘,那邊溫度更舒服,但很快被保安叫醒。冬天夜裡溫度低,凍得待不住。他回憶,十二月某天,有個小伙子光腳穿拖鞋,凍得直抖腿,帶着桌椅吱呀吱呀聲音很大。凌晨四五點,一個高高壯壯的中年男人過去提醒,態度和氣,小伙子卻反應激烈,吼了一句:「滾!」男人也被激怒了。
鄢悅稍晚些在門口遇見那個被吼的男人,把手裡用礦泉水瓶做的熱水袋遞給他,對方拒絕。他碰了下那人的手,冰涼,「還說不冷,騙誰呢?」男人沒接話。後來鄢悅看到他也拿了一個礦泉水瓶去接熱水。那次之後,圖書館溫度調高了不少,他不清楚這之間有沒有關係,「倒是凌晨兩點,民警會上門查身份證。」
王林森跟鄢悅聊天的第二天,去面試一家造船廠,「雖然辛苦,但能學到一技之長」。他打算如果面試成功,就不會再回書店了。
過去兩年,他過夠了打零工的日子,外賣員、飯店服務員、超市收銀員、物流員、網約車司機、群演都幹過,在各種兼職之間橫跳,「我之前覺得在這個社會接觸得越廣,機會就越多,就能找到一個真正適合我的職業」。
王林森是河北人,2017年中專畢業後入職一家湖南的環保企業,做廢氣處理。他形容自己笨手笨腳,抽管子彈到師傅臉上,幹了四年多始終在做一些基礎活。工資6千多,需要常去外地出差,有時還要上夜班。相親見了兩面的女孩嫌他工作不穩定,還有女孩聞到他身上殘留的硫酸味,露出嫌棄的表情。
他就這樣離職,到大城市闖了兩年多,留下一些令他不想回頭的片段:比如跑15個小時網約車,累到用礦泉水瓶墊在腰椎緩解疲憊;零點後結束群演,捨不得打車回家就坐環線公交到天亮。
他很難說清自己的狀態,「一會隨遇而安,一會兒勇於探索」。勞力性工作他覺得沒挑戰性,沒什麼技術難度,做一段時間就不幹了。也幻想過一夜成名,像王寶強一樣,但最終發現自己沒有一技之長。
來上海四天,王林森面試過三份工作。人事助理崗,面試沒怎麼問專業,倒是讓先交1400塊買兩套工作服。汽修小工需要專業度,即使他願意從學徒做起,人家也不收。還有一份工作,招大學的會議服務人員,因為身材寬,套不進現有的制服,穿着便服幹了幾個小時,就接到委婉的辭退電話。為了那次面試,他特意買了雙黑皮鞋,「挺有吸引力的,工資5500,雖然過年不回家,但活兒很輕鬆。」
鄢悅仍在圖書館裡過着臨時生活,他過年沒回家,上次跟父親聯繫還是去年八月。在腰包深處的夾層里,他藏着一封父親十年前寫給他的手寫信。跟別人聊到興起,他會掏出來。
打開一層塑料袋,再打開另一個袋,他精確記得寫信的日期,2014年3月2號,卻故作瀟灑說:「我還真不記得內容了。」折得整整齊齊幾頁信紙邊緣已起了毛,破開了口。「鄢悅,我希望你做一個『土豪級』的有志青年,所以送你一個土豪金的『土豪級』手機。」父親給他買了一部蘋果手機,iPhone5S,那是他人生第一部智能手機。
他指着信里那句「不想左右你的想法」笑起來,像是自言自語,「他肯定是沒做到,因為他忘了」。
(文中人物除鄢悅和王林森外為化名。)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
本文由看新聞網轉載發布,僅代表原作者或原平台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立場。 看新聞網僅提供信息發布平台,文章或有適當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