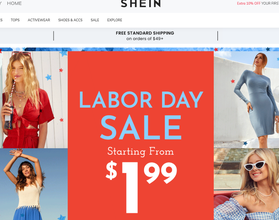通訊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我確信,任何一個僑居海外的中國人,或者是僑居他國的任何一個異鄉人,只要他想,周末或者任意的那一天,拿起電話,就可以撥通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角落,向其親人傾訴衷腸!
包括那些堅決反共、僑居海外的中國異議人士,也包括那些逃離戰亂頻發的阿富汗、索馬里、敘利亞的難民,他們都可以利用發達的現代通訊工具,和父母、親人敘說思鄉之情,打聽鄰里朋友的消息;有些中國異議人士,還能將父母接出來在海外團聚,有的甚至還能返回中國探親訪友。
但我們維吾爾人卻不能,世界上哪怕是最貧窮、最不發達、戰火紛飛的國家或地區的百姓能夠享受的基本通訊權力,我們沒有,也都被中國殖民者無情的剝奪!
周末給家裡打電話,對我們維吾爾人而言,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更多的時候是一種痛苦的折磨;我們既無法打通電話,也不能將父母接出來;更甚,我們絕大多數的維吾爾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親人是否還活著,更遑論知道鄰里朋友消息了。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多力坤.艾沙先生,先是在去年的年初,輾轉得知母親幾個月前已在集中營去世;然後,在今年年初,又通過中國環球電視網的宣傳視頻得知,父親也已去世幾個月了;但不知道是甚麼時候、在甚麼地方去世的。
澳大利亞的女詩人法特瑪(Patime)女士,也是在最近輾轉通過聯合國得到了消息:她苦苦尋找的父親,已經在幾個月前去世了。
另一位在土耳其的維吾爾父親,在尋找回國探親妻兒一年多之後,突然,在中國環球網宣傳維吾爾兒童『幸福生活』的視頻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個兒子,然而,他的妻子和其他孩子仍然是杳無音訊。
和大多數維吾爾人一樣,幾個月前,我也通過不同渠道,輾轉打聽到的消息是:我母親還活著!
但幫我打聽的人都沒有親眼見到我母親本人;一位朋友告訴我,我給的電話號碼那邊的一人打過去,確有一位維吾爾老人接電話,根據口音確認應該是我母親;另一個朋友通過他人打聽到伊利夏提的母親還在;但都不是百分之百確定。
這輾轉傳來的消息,一點都沒有減輕我的焦慮。
如何確認母親還健在的消息,使我在痛苦中煎熬了一兩個月,上個月底,我依然決定無論如何,一定要打個電話,哪怕是不說話,聽一聽母親的聲音也行;已經有四年沒有聽到母親的聲音了;衹要電話打通了,母親一定會說甚麼,我能確認母親的聲音;只要聽到了母親的聲音就可以稍微放心了。
兩星期前的一個周六,起了一個大早,開車來到家附近一個寂靜的小公園,把車停好,然後拿著手機稍微猶豫了一會兒,最後毅然決然地撥通了電話,「嘟嘟、嘟嘟嘟……」;似乎是極其漫長的等待之後,傳來一位漢人女士清脆的聲音:「您撥打的電話是空號……」,查一下號碼,再打過去,仍然是沒有人接,嘟嘟之後,還是那位漢人女士清脆的聲音。
一兩個月來的忐忑不安,焦急的期盼,又轉為了無盡的憂慮和煎熬!怎麼會是空號呢?不是那邊打電話有人接了嗎?
這是自2016年8月底和母親最後一次通話之後的第幾次呢?我也不記得了,我像個病人一樣,每隔幾個月,實在受不了那種思念、那種母親是否還健在之不確定的煎熬時,會打個電話試一試;每次都是那無情的清脆之聲粉碎我的僥倖夢想。
兩個月前,有人輾轉從歐洲給我傳來消息:我的大妹妹和二妹妹,在奎屯的一個集中營里關押著,消息源因擔心其還在家鄉親人的安危,不能站出來;根據傳來的消息:大妹妹,和二妹妹及她的丈夫、大女兒都在奎屯集中營。
兩個妹妹在集中營的消息,既是預料中的,但又是我刻意迴避面對的一個事實;但一經確認,仍然使我完全陷入痛苦中不能自拔,憤怒、悲觀、內疚、自責、無助,時時刻刻折磨著;白天工作無法專心致志,晚上,輾轉難於入睡,常常是半夜醒來一個人坐著發呆。
每天從早到晚,滿腦子是問題,大妹妹是單身母親帶兩孩子,一女一男;二妹妹兩個女兒;大妹妹的兩個孩子在哪兒?他們也在集中營嗎?二妹妹的小女兒在哪兒?三妹妹一家四口,她們在哪兒?也都在集中營嗎?是在哈密的集中營呢,還是在別的甚麼地方?假定母親在家,那誰在照顧她?
電話鈴響了,把我從無頭緒的無數個「為甚麼」中拉回了現實,是妻子打來的,問我去了哪兒?大早晨怎麼不在家;我吞吞吐吐的告訴她,我在家附近小公園,試圖給母親打電話;「你怎麼這麼自私呢?你證實了母親的健在能改變甚麼?你給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給你的妹妹帶來的還不夠嗎!我不也一直沒有消息過嗎,你就不能忍一下嗎」話沒有說完,電話那頭妻子的聲音開始哽咽了。
我默默地聽著,妻子最後哭著說完:「這是甚麼日子呀,甚麼時候是個結束啊!」就放下了電話。
我機械地啟動汽車,在茫然中無意識的將車開回了家。
新的一天,這個除了維吾爾人以外,地球上大多數人都以睡懶覺、與父母親人分享歡樂的周末,對我這個維吾爾人而言,要從擦乾自己的淚水、舔舐自己的創傷,用自己都不太相信的空話,安慰同樣沉浸在無盡思念親人之痛苦煎熬中的妻子開始。
本文由看新聞網轉載發布,僅代表原作者或原平台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立場。 看新聞網僅提供信息發布平台,文章或有適當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