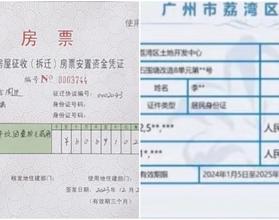車輪上的人們,始終等待着那條真正看見、接納他們的通道。
文|馮蕊 黃子睿 丁立潔
編輯|王瀟
約113公里長的黃浦江上有18條隧道。代駕趙偉還未能從中找到一條安心回家的路。
轉機在一個月前出現。自2月16日起,每天深夜11時至次日清晨5時,復興東路隧道上層允許電動車試通行。這是上海第一條專門、合規開放給非機動車的跨江通道。
截至3月底,隧道入口的值守人員統計,每晚從兩岸穿越的電動車數量在1400到1600輛之間,其中大部分是代駕,剩下是外賣員、地鐵維修工、結束加班的職員。他們鏈接着2487萬人口的城市在深夜不斷生長的需求。
他們自身樸素的需要,卻常常湮沒在飛馳之中。當車輪下的路程越來越長,車輪上的人們,始終等待着那條真正看見、接納他們的通道。

01
復興東路隧道的浦西入口是片老城廂。在這裡,深夜總是靜悄悄的。
但2月16日晚,電動車一輛挨一輛排了數十米長。不時有記者穿梭在人群的空隙間,舉着手機直播、採訪。
28歲的騎手陶水排在隊伍的首位。當三四個話筒圍攏過來,他有種說不清的自豪感。
「我是第一個跨江的。」陶水強調,「不罰款的那種。」
去年12月,他在送貨時違規穿越復興東路隧道,被罰了50元,而一筆跨江訂單的配送費不到40元錢。這般經歷,此前在騎手中是常態。
晚11點整,隧道口的路障徐徐撤離,信號燈變成綠色。
三十餘輛電動車,如同被喚醒的魚群瞬間湧向入口。口哨一聲接一聲響起。
「慢一點、慢一點!」交警焦急地勸導,「(限速)15公里,都開慢一點啊。」
此刻在浦東入口,劉飛第一個開着電動車進入隧道。「很寬敞、很空曠。」在沒有汽車的兩條道路上,他嘗試放下速度、自由地騎行。
從這周開始,他「至少有了回家的方法」。晚上來浦東的朋友家聚餐,他不再擔心多聊兩分鐘而錯過9點半的末班輪渡。
隧道開通的當晚,根據官方統計,電動車過江由西向東247輛,由東向西242輛。

消息很快在網絡擴散,更多人聞訊趕來。
2月17日,在陸家嘴上班的余崇光特地熬到11點前來體驗。他打轉許久才找到隧道的入口。「很新鮮,效率高多了。」他騎小電驢通勤6年,第一次在5分鐘內跨過黃浦江,以往時間都在30分鐘以上。
3月8日,代駕杜宇跑單後騎到隧道。張望到有人站在入口,杜宇慌張起來,「是查電動車的嗎?」他騎過去輕聲詢問。
「你可以走。」對方朝他招了招手。杜宇這才鬆口氣。他曾因「違法」感到憂心,只跟着代駕的老師傅或戴上口罩偷偷穿越過幾回。
3月22日,管理人員張陽已經熟練地指揮通行。
他緊緊盯着前方,每駛入一輛電動車,都要划動一次計數器。一個多月來,他看着手裡的數字從每晚250、500跳動到近800。
「對面的情況差不多。」張陽感慨,「還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隧道)。外賣和跑代駕的曉得。」
早上5點前,張陽都要守在這裡。他的腳邊放着一隻保溫杯,陪他熬過整夜。
02
數字背後的車輪,鏈接着一座城市的運轉。
晚上11點半,地鐵檢修工人張景剛剛上班。此時在各大地鐵站,列車陸續停止運轉、回到車庫檢查。在龐大的設備系統中,每個零件都有不同的生命周期。
張景的工作,便是在部件老化之前換掉它們,減小地鐵出現故障的概率。15年間,公司的檢修網絡覆蓋到全部517座車站,張景往返過其中近300個站點。
深夜的道路上,同樣傳遞着緊急的需要。
陶水三年前剛到上海,便成為外賣騎手。一些平台開放了「全城配送」的業務,騎手分為「專送」與「眾包」。與「專送」不同,陶水作為眾包騎手,沒有平台與範圍的限制,能夠在全市自由搶單。
他送貨的距離逐漸從5公里拓展到50公里、80公里,平均的配送時長卻從60分鐘削減到35分鐘。保溫箱裡原先是麻辣燙、螺螄粉,現在一半空間給了相機、衣服、汽車配件。他經常遇見,跨城通勤的上班族回到蘇州家裡,才發現鑰匙和身份證遺落在了陸家嘴的辦公室。
按照陶水的說法,儘管輪渡停航後,系統不再自動給騎手派發跨江業務,但這些需要常常以普通訂單的形式,出現在「搶單大廳」中。一些單子標註着「商家配送」,實則也是店主尋找騎手服務。
承擔風險的責任轉移到他的身上。陶水算過,深夜跨江的訂單平台不派、新手不敢送,配送費就能漲到普通單子的六到七倍。他主動搶下了生意。

交際與消費的欲望,也從白晝蔓延至黑夜。
趙偉在四年前干起代駕的兼職。每晚8點,從工廠下班的他換上馬甲,開啟接單頁面。
他在兩家平台上切換賬號。在其中一家平台上,他已經跑了2119單。他曾三次遇到同一位男人,對方從不提自己的職業,永遠在打電話,談論「明天去哪應酬」;他曾在深夜12點的農村見證過商業談判的酒局,在沒有路燈的村莊迷失方向,被5隻野狗追逐。他看見「酒駕入刑」後,一些公司老闆哪怕離家只有兩公里,也不敢冒風險僥倖開車;很多時候,他甚至見不到乘客,越來越多人不再親自去取維修、購買的車輛,趕在夜晚4s店歇業前選擇了代駕。
只要趙偉沒關頁面,系統就會自動匹配訂單。在90%的夜晚,他都被算法甩到了黃浦江的對岸。尤其是周五,工作一周後的人們擠在延長營業到凌晨的飯店、酒吧。
此時,陸家嘴的燈光並未休止。從事IT行業的余崇光通常在晚上8點下班,每個月,他總有一兩天加班到十點之後。他覺得比起其他IT公司的「996」,這是一份還算不錯的工作。
在附近的商圈,一位火鍋店的職員在晚11點剛剛結束忙碌,準備騎車返回對岸家中。她沒來得及換下工作服,一陣暖風吹過,空氣中散發出牛油的氣味。
03
隨着城市越轉越快,新的需求出現在規劃以外。
張景記得,最早上海有通宵的渡船。然而隨着軌道交通與橋樑建設,輪渡公司開始出現營收的難題。2015年後,黃浦江上最後一條通宵航線退出歷史。
一段時間裡,清晨4點下班的張景就蹲在站點外的馬路牙子,等到5點半之後第一班地鐵開放。後來他決定騎着兩輪車通行。
趙偉剛入行時,每晚都有往返於浦東、浦西之間的「夜宵公交」。凌晨兩點的那一班上幾乎全是代駕,走道里堆滿了摺疊的電動車。
2022年初,上海修訂了公共汽車的乘坐規定,指出代駕車的鋰電池容易爆炸、存在安全隱患。公交司機不再允許代駕攜帶電動車搭乘。
從那之後,趙偉看見灰色營運的「打撈車」出現。一過凌晨,在浦東外環的匝道出口,每十分鐘、二十分鐘有一輛「金杯」「全順」品牌的麵包車經過。瞄到代駕師傅,車主搖下車窗喊道:「要去哪裡啊?一人只要25到30。」
車上的座位已經拆除,車廂後半段安裝了鐵架放置電動車。最擁擠的時候,趙偉和所有人貼在一起,不敢動一下腳尖。儘管如此,經過徹夜工作,許多人都能站在這裡睡上好覺。
這些車輛往往出沒在陸家嘴的20公里之外,整車拉滿人要一到兩個小時。等到四、五點天色漸亮,它們便消失在道路上。
此刻在這座城市,留給電動車的合法通道只剩下17條輪渡路線和3座大橋。

有幾回,加班後的余崇光騎到楊家渡渡口時,22時30分的末班船已經開走。他只得把電動車留在公司打車回家。在十公里外的金橋路渡口,一位剛下班的職員騎行5公里,趕上了23時40分,黃浦江上最後一班渡船。他的電動車只剩下1%的電量。下船的地點離家還有5公里,他不敢把電動車仍在原地,半小時後,他加價到60元,等來一輛貨拉拉。
深夜配送時,系統給陶水的時長仍然按照輪渡計算,不會向顧客收取騎手繞路的費用。陶水考慮,有「超時」和「差評」的出現,他會被扣分、扣款;而通過隧道,往往只要三到五分鐘。
他計算過,違規穿越隧道,被罰的概率只有5%,這些單子的收入遠遠抵消了這筆罰金。
在一些代駕平台上,趙偉直到坐上對方的汽車,才能看到終點。在「客戶至上」的規則里,他很難有拒絕的權利:代駕主動取消訂單,會被平台判定為「有責銷單」,一次扣除3分。每位代駕共有12分,一旦被扣完,賬號自動取締。
他試過當面向客戶請求。「老闆您好,」他頓了頓,放低語氣,「我是兼職做代駕的,第二天要上班,這個時間到浦東,我是回不去的。」
有時對面會爽朗地按下撤銷。另一些時候,對方直接拒絕,或是醉酒發了脾氣。趙偉裝作什麼也沒發生,接着跑單。
四年前,他第一次被「甩」到浦東市區時,已是凌晨時分。
最早一班輪渡將在5點開放,三座大橋距離他都在40公里以上。他只得開着導航往家的方向騎,隧道成了必經的跨江路徑。
04
當時離趙偉最近的便是復興東路隧道。抵達入口時,他猶豫了許久。
趙偉明白,隧道禁止非機動車通行,其實是出於安全的考量。
在國家的安全規範里,長度大於1000米的隧道不得在同個孔內設置非機動車道和人行道,以免混行發生安全事故。
何況隧道下坡鋪着凹凸不平的減速帶,還有不少排水的小渠。他和杜宇描述,僅僅兩厘米的高差,就容易卡住一輛代駕車的輪子。代駕電動車比一般的電動車要輕,一旦車輪陷入,車上的人幾乎都會向前、摔倒在地。
但此刻,「騎車入隧」成了無奈的決定。
趙偉打開頭盔上的爆閃燈,能夠在黑暗中提醒汽車避讓。隧道下層有條廢棄的摩托車道,他緊貼着最右側的路沿向前騎行。
騎到中途時,趙偉突然感受到一陣大風撲來,吹得電動車身劇烈搖晃。有輛汽車正從他一米外的距離駛過。
「嘟——」聽到汽車的喇叭聲,趙偉越來越慌。把速度加到四十碼,恨不得立刻駛離出口。
事後他對自己的冒險後悔不已。代駕平台有專門負責司機管理的部門,出了安全事故,會有司機拍攝視頻、照片發在部門群聊里。
他時常看見,群里有騎電動車摔成骨折、受傷的人,不少是在穿越隧道時發生的事故。他心裡有種說不出的滋味。「這種事情哪天會不會也發生在我身上?」
何況在他的行業,「出事」更意味着失業的風險。
趙偉看到,不少代駕在平台上報事故、申請保險。沒過多久,賬號被封禁、管控。事故嚴重的人,容易背着「不安全」的標記,很難再重新步入這行。
他們常常默默消化了事故的發生。趙偉每次摔跤後,就去衛生中心買藥回來擦下傷口。撞到其他車,他會自己掏些錢賠償。他從沒聯繫過司管部門,在手機里設好提醒事項,「今天一定要戴護膝」。
有一天,他和妻子說,「我把手機定位在你的手機錄入一下吧。」
趙偉永遠不知道,下一刻他會去往城市的哪個角落。「我害怕出事,沒有人知道我在哪。」感受到妻子的擔心,他變了語氣,「開玩笑的」。
杜宇同樣在群里看到事故的視頻。他曾經在通過減速帶時,差一點就摔了跤。回想起來,他始終感到不安。
他開始站在隧道的100米外,搶順風車的單子通過隧道,通常前半夜要十多塊錢,後半夜不到十元。
兩三個月後,他「真的不捨得」花這筆錢,下定決心,「騎吧,只能騎。」他騎了20公里繞到最早開放的渡口,等着4:40第一班船。這樣一來,下船後他還能騎到熱鬧的市區繼續接單。
後來他發現,每天0點到3點之間,許多隧道要養護,這時會有一條車道封起來,擺上反光筒、反光錐。遇見代駕經過,作業的工人往往靠在一邊,讓出一條路來。
一次他在偷偷穿越時撞見了交管人員。
杜宇感到害怕,他聽說過有深夜執法抓到了代駕,罰款從20到50元都有。
「你走吧。」一位交管人員朝他喊了一聲。緊接着補充,「注意安全!」他勸道,穿越隧道很危險,下次不要這樣了。
「好。」杜宇舒了口氣。

05
在更長的人生里,趙偉也在等待路的出現。
16歲前,他在大山里長大,願望是成為軍人。當時老家有一面很大的黑板,寫上那些成功入伍的名字。
他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黑板上,沒過一禮拜,卻被抹掉替換成了「張偉」。他第一次覺得看不到未來,從大山跑了出來。
17歲的大年三十,他坐着火車來到上海,那節車廂只有他一人。
他找到青浦的汽車工廠上班,認識妻子、成立家庭。四年前,女兒無法就讀上海的初中,妻子辭職陪她回老家念書。他又成了一個人。
躺在十平米的房間,趙偉時常感到孤獨,還有一種越發沉重的擔子。他想讓時間走得更快。
有一天,趙偉在抖音上刷到代駕的視頻。看到行業正值鼎盛時期,他想要試試。
他第一次感覺自己充滿幹勁。每個晚上,只要出去跑單都會有兩三百元的收入,一個月掙的錢。剛好能抵上孩子的開銷。
但變化逐漸在行業發生。趙偉居住的鎮裡,代駕數量從40、50增長到200多個。好幾個晚上他出去等單,最後面對着頁面里「0」的數字。
趙偉卻不敢停下車輪。他說,每天一睜開眼,總會想怎麼樣才能多賺一點。他說,手頭上有點積蓄,生活才能有安全感。

與趙偉不同,陶水曾覺得生活有很多條路。
高考失敗後,他從老家徐州去廣東謀生。有商家做活動搭了舞台,他在台上鋪了張墊子,睡了整整兩晚。
後來他數不清自己幹過哪些活,有搬運工、保安、群演,還賣過手機殼。三年前,他在深圳租了倉庫,企圖抓住電商的風口,結果沒掙三個月的錢就欠了一身債。他去剪了頭,來上海「從頭開始」。
剛到城市時,他從火車站、陸家嘴一路騎到了迪士尼,又到蘭州、武漢各地打轉。這份沒有社保的工作,反而讓陶水感受到自由,「今天的錢拿到手,明天就可以不幹了。」
直到今年2月,他在醫院確診了二型糖尿病。沒有單位繳納的保險,他花了2000多元做了檢查。
治療與飲食的限制,讓陶水週遊各地的旅行計劃擱淺,他從醫院回家後,在床上躺了八天。
陶水突然失去了方向。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仍然需要那絲微小的保障。
然而,這些需要很少在日光下顯現。
杜宇說,大家沒有公開表達過通行的需求。「我們去說的話,是不會有人受理的。」他篤定,反而會讓別人覺得自己怎麼這麼愛反映問題。「我潛意識裡就覺得這樣是不行的,會被當作一個負面的典型處理。」
陶水在抖音做起賬號,把生活中沒有說出的苦惱、控訴放在了網絡上。粉絲很快就漲到1萬。
這和他在橫店做群演時的感受完全不同,當時他演了一個路人甲,走來走去、沒有一句台詞,「沒人看見、記得這個角色。」陶水說,自己始終沒有忘記。
06
直到轉機發生在現實的世界裡。
今年2月,杜宇無意間刷到新聞,「復興東路隧道上層將開放電動車通行。」
他第一反應是,「假新聞吧?」此前他聽過類似的風聲,那是一條有着上下兩層的隧道。他去入口看過許多次,雙層都還是汽車在飛馳。
真正到了現場,他有一種「安心」的感受。
隧道開放以來,他已經騎行了十多次。比起其他隧道,這裡的上層坡度要更緩一些,長度比下層短了一千米左右。
他驚訝地發現,在隧道的浦西出口,綠化帶的一段被打開放上黃色的隔離欄,改造成一條非機動車道。交警值守在那裡看護着最後一段紅綠燈。
杜宇和陶水坦承,在這條隧道以外,城市裡仍有許多被阻斷的跨江通道等待打通。「隧道承接的主要是右半邊的區域,其餘地方還是打斷的。尤其在浦江鎮、周浦那一塊兒,有許多跨江的需求。」杜宇說。

但看見才能成為改變的起點。
在家休息時,陶水接受到平台的入職邀請,這是一個有社保的配送崗位。
陶水猶豫後選擇了拒絕,他已經習慣問自己,下一站要去哪裡。在做出選擇以前,他又奔忙起來。「像我們這種人,一天工作五個小時算是很長的休息。」
趙偉開始思考人生新的可能。他說,在車輪上,他看到了一個流水線以外更大的世界。
去年底,有客戶在下車時突然問他,「能不能留個電話?」他說自己是做產品的,趙偉性格隨和,和人溝通起來很舒服,「我需要這樣的業務人員。」
趙偉也有顧慮,變化對37歲的他而言「沒那麼容易」。他還想再干一段時間的代駕。深夜的騎行是他一天中最放鬆的時刻,現實的焦慮被拋在腦後,他仿佛又回到了大山里那段自由、年輕的時光。
杜宇仍然記得六年前的決定。一個朋友告訴他,自己在上海乾了四年外賣,從早到晚跑,終於攢錢買了房子。和杜宇在短視頻里看到的財富神話不同,那是一段普通人堅持下來得到回報的故事。
杜宇卻因此受到觸動,隻身來到這座城市。在越轉越快的世界裡,他始終相信那些最笨拙卻最踏實的通道。他想繼續騎下去。
(文中受訪者除趙偉外均為化名)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原點original
本文由看新聞網轉載發布,僅代表原作者或原平台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立場。 看新聞網僅提供信息發布平台,文章或有適當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