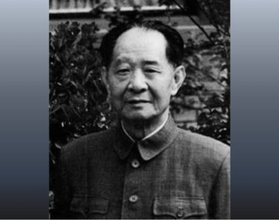南京學運同樣風起雲湧、驚濤拍岸
譚嗣同說過,中國兩千年之政,秦政也。所謂秦政,至少包括兩方面:皇帝一人獨裁和首都中央集權。共產紅朝號稱反封建,卻把兩者全盤繼承下來。過去,北京是帝都;如今,北京是共產黨的權力中樞,毛澤東晚年曾對來訪的尼克松說:「我無法改變整個世界,我只是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方。」在當代中國,北京中心主義根深蒂固,北京汲取全中國各種資源,以供盤踞在此的統治階層自肥,而關於首都北京的論述,也一葉障目式地成為關於全中國的論述。
耐人尋味的是,即便是反對派的論述也遵循北京中心主義原則。比如,長期以來,對八九民運史的書寫就始終以北京為中心,刻意忽略其他省份和城市。這場運動被稱為天安門運動,但實際上,這是一場席捲全國的民主運動,天安門是一個關鍵場所,但絕非全貌。澳大利亞學者林慕蓮在《重返天安門》一書中揭露了發生在成都錦江賓館的另一場屠殺,在成都長大的我居然第一次知道此真相。可見,「在地」者其實是多麼地「離地」。
八九民運應當是一幅全國拼圖,每個地方的參與者都有責任拼上自己那一塊馬賽克。南京學生領袖吳建民的回憶錄《歲月有痕》,為之拼上了關於南京學運的關鍵部分。吳建民出生於高級軍官家庭,當過兵,在南汽集團工作過,一九八九年,他即將從江蘇商業幹部管理學院畢業,學運爆發後,他全身心投入其中,一生的軌跡因此改變。與大部分直接從高中考入大學的本科生相比,他當時已二十六歲,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和社會經驗,有勇有謀,妙語連珠,也有組織管理才能,很快就脫穎而出,成為南京學生領袖之一。
南京高校的數量、學生在校人數的規模,在全國排第三,僅次於北京、上海。在這本回憶錄中,吳建民詳細描述了南京學運的過程和特徵,與北京學運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其特色。南京高校以南京大學為主,迅速模仿北京成立了一個指揮南京地區學運的指揮部「南京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前後任職常委的七個同學,清一色是南大學生,外校學生一個都加入不了,這在北京學運中是不可能出現的情況。在南高聯之下,又建立「參謀部」,「參謀部」匯集各校的骨幹,每天處理日常事務,這是北京學運中沒有的建制。
學運過程中,吳建民提出「北上運動」的構想。他認為,南京作為民國故都,有民主血液,南京的學運領先於南方各城市,所以不能滿足於一城一地,應當率先發起「北上運動」,步行前往北京,沿途將安徽、山東、河北、天津的學生都動員起來,像滾雪球般壯大。當這支隊伍走到北京時,就有條件在北京組成「全國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然後以「全高聯」而非「北高聯」的身份與中共當局對話。
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南京學生組成「南京高校北上民主長征團」,從鼓樓廣場出發,徒步前往北京。吳建民任「北上指揮部」副總指揮。這支數千人的隊伍,一路突破圍追堵截,六月三日,到達安徽滁州師專集結休整。六月四日上午,隊伍本要出發,天上下起大雨,不得不等一等。他們還不知道,北京已發生了一場大屠殺,這場突如其來的大雨,似乎是悼念死難者。江蘇和安徽兩省派來大量客車已攔在隊伍前面,且還有很多荷槍實彈的武警。前來勸誡的江蘇省常務副省長兼教委主任楊詠沂告訴吳建民,北京已清場,現場的武警將不惜一切手段阻止學生前進。吳建民和指揮部其他人員被控制起來,大部分同學都被推上大客車帶回南京。少數先遣隊同學騎自行車到了張八嶺鎮,遭到武裝民兵攔截,並威脅說:「再往前走就開槍了!」最終「六四北上」的終點站,就在張八嶺鎮畫上了句號。
屠殺之後的抗爭,更是可歌可泣
被帶回家後,吳建民被軟禁在家一個星期,然後回到學校。六月二十日,南京市公安局發布「南京市高自聯通緝名單」,他名列其中。學校保衛處官員把他帶到公安局。隨後,尚有良知和風骨的學校王院長將其保釋出來,讓其參加畢業考試。但上級命令扣下其畢業證書,並要求他每天到「清查辦」交代問題。
當時,吳建民和其他南京學生領袖聽說香港有「黃雀行動」,但他拒絕流亡海外,對逃入美國使館的方勵之夫婦無比失望,「導師跑了,丟下萬千他的追隨者跑了!……那我們這些學生怎麼辦?我們也可以跑嗎?大使館裝得下成千上萬的參與六四學潮的學生嗎?」他表示:「我反對臨陣脫逃!反對當中國民主碰到困境時就選擇逃亡國外!」他慷慨激昂地對同仁說:「我願意付出青春、付出熱血,比起那些已經在天安門廣場死難的同學,我們責無旁貸,應該留下來堅持!」
隨後,吳建民發動大家辦刊物、建立組織,完善「後六四時代」的抗爭機構。他到上海、肇慶等地與香港支聯會派來的人碰面,對方帶來資金資助。二十多年後,吳建民流亡美國,原本計劃到香港向支聯會致謝,香港局勢卻江河日下,支聯會被迫解散,他本人根本不可能入境香港。
此時的吳建民,經過「六四」屠殺,已完全看清中共的邪惡,有了明確的政治目標——推翻中國共產黨,結束中共一黨專制,為「六四」死難者討回公道,為中國人民爭取自由解放,為實現一人一票的公平自由民主選舉,實現十四億的人民人人過上有尊嚴的生活而奮鬥。
一九九零年春,吳建民在鼓樓大街鍾亭約見南京幾所高校的主要學運領袖,和大家交流了建立組織機構的想法。他們討論組建「中國民主前線」,並設立最高常務委員會,吳建民被推舉為主席,副主席為彭萬忠、李勇,李力夫任秘書長兼常委,委員有王立軍、王小泉、段小光、王建華、劉格等,他們大都是學生或青年教師。這些反抗者都不為外界所知。
一九九零年代初,在中國其他地方,如北京、成都、廣州、杭州等地,類似以秘密組織的形式展開反抗的群落還有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語言學院年輕教師胡石根等發起的「中國自由民主黨」活動,僅在北京就有數十人被捕,被判刑的有十五人,也稱「十五人案」。西北大學有張明案,蘭州大學有丁矛案,成都也有廖亦武等人的「大屠殺電影」案。「六四」前參加民主運動的人,有不少是隨大流,也有不少是投機者,因為人們普遍樂觀評估這場民主運動可能會成功;「六四」後仍然參加民主運動的人,才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衛填海式的真英雄,因為此時的反抗無異於以卵擊石、螳臂檔車。
過去,由於資訊有限,我曾撰文批評,中共槍聲一響,反抗運動灰飛煙滅,比不得韓國的反抗運動——光州事件中,全斗煥軍政權殺人的兇殘一點也不亞於中共,但韓國的抗爭一直此起彼伏、前赴後繼,韓國人似乎比中國人更有血性。但後來當我陸續讀到廖亦武、劉賢斌、吳建民等人的回憶文章和回憶錄,就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中國不是沒有魯迅所說的「埋頭苦幹的人,拼命硬幹的人,為民請命的人,捨身求法的人」,只是他們「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就連在文革最黑暗的時代,楊小凱在獄中也接觸到各式各樣組黨反抗暴政的勇敢者,只是他們都被屠戮殆盡。中國未能像韓國那樣實現民主化,不是因為中國人比韓國人更怯懦,而是因為中共政權比韓國軍政權殘暴千百倍。反抗中共暴政,需要具備前所未有的勇氣、智慧和韌性。
他的刑期之長,超過二十一名被全國通緝的北高聯領袖
吳建民等人低估了共產黨的邪惡和人性的幽暗,他們的一舉一動早已在中共國安部門嚴密監控之下。幾個月後,國安部門就收網了,他與同仁紛紛被捕。多年後,他從獄中歸來,才知道他們的組織早已被中共滲透。與他一起赴外地會晤支聯會代表的女同學吳蔚,向當局供出若干只有他們兩人知道的行動細節。他出獄後在中國生活了十八年,其間慢慢與當年南高聯的成員恢復聯繫,只有吳蔚從未出現過。另一名經吳蔚介紹進入地下組織核心圈的女同學羅明娟,當時負責開設賬戶存入香港支聯會轉來的幾十萬資金,案發後此人一度人間蒸發,那筆巨款也不翼而飛。吳建民出獄後才知道,羅明娟順利在南大完成學業,然後到廣西國安廳工作,他這才恍然大悟——這個女生最初就是當局安插在他們身邊的臥底。吳建民也認為,那個唯一名列全國通緝令名單、日後在美國混得風生水起的南京學生領袖也是同一類人。中共是靠搞地下活動和秘密組織起家的,這些單純天真的學生的所作所為,在其眼中如同過家家般幼稚。
國安部門一開始企圖誘騙吳建民充當線人,聯繫香港支聯會人員來內地與之會晤,然後將來人一網打盡,卻遭到吳建民嚴詞拒絕。當局將不予配合的吳建民重判十年,他的刑期比全國通緝的二十一個學生領袖都長。江澤民以是否重判「六四」學運領袖作為各省站隊的態度。緊跟江澤民的省份,自然向中央獻投名狀,對本地學運領導人判得很重,受刑人在獄中的待遇也更惡劣。當年被關押在秦城監獄的劉曉波,後來讀了廖亦武在四川坐牢的回憶文章之後感嘆,廖亦武坐的監獄猶如地獄,與之相比,他在北京的監獄中簡直如同天堂。
吳建民在回憶錄中詳細講述了自己從看守所到監獄的鐵窗生涯,他曾被上「半步鐐」,被單獨關押在長寬只有三米、以黑色橡皮封閉的號房裡,巨大的頂燈二十四小時都照着人。他多次遭受國安人員、獄警、牢頭獄霸酷刑折磨,他說:「我唯一能保護自己的方法,就是不怕打!」最恐怖的一次,他被帶到操場上,有犯人蹲在一個圓圈中,周圍有六頭狼犬眈眈相向。警衛紅旗一揮,六頭狼犬就撲上去。犯人抱着頭,趴在地上嗷嗷慘叫。獄警嚴厲警告:「你不服從管教,下次就輪到你了!」吳建民差點嚇得暈過去,他寫道:「這一次觀刑體驗,讓我直接感受到,在中共的血腥歷史上曾經多次發生過、有多少普通犯人被帶出去觀斬、看其他犯人被槍決的血腥場面!我不知道,古今中外還有哪個政權、哪個政黨能比中共更邪惡、能比中共更殘暴!這個場面給我的刺激很大,以致多年後,我經常在夢中夢到這一幕。」他在獄中聽說有一些犯人配型成功後被活摘器官,他的老軍醫的父親悄悄告訴他一個辦法,讓他體檢時尿液含血量超標,由此逃過被列入器官移植名單。
吳建民被捕後不久,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貝克訪華,向中方提出釋放政治犯的要求。與之會談的中國外長錢其琛在回憶錄中寫道:「名單中有『吳建民』其人,我向貝克說,我們的新聞司司長叫吳建民,正在現場。此時,吳建民答道:『在。』貝克見狀,反應還算機敏,馬上說:『你放出來了。』引起鬨堂大笑。」從此細節可看出,中國的「戰狼外交」不是近年才出現的,錢其琛一副痞子無賴嘴臉,裝瘋賣傻、李代桃僵,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還將該細節寫入書中,殊不知這是要遺臭萬年的。貝克奉老布什之名訪華,要跟中國恢復商貿關係,對這種惡作劇無從深究。二十多年後,貝克在美國會見流亡出來的吳建民,當初他對包括吳建民在內的名單上的政治犯或許確實真心關切,但受制於美國的對華外交政策,無數像吳建民這樣的良心犯最後就被忽略不計了。
一九九零年代初,因中國擁有數億奴隸勞工的「低人權優勢」(用今天的說法就是「韭菜」和「人礦」)及龐大的市場,西方迫不及待地把「六四」翻篇,把中國納入經濟全球化體系。在此背景下,中共政權重新恢復了自信,學者白信評論說:「中國政府在一九九零年代與美國國會的年度最惠國待遇談判中,玩弄以異議人士換市場的人權政治,從而不僅逃避屠殺責任,也逃避真正的人權責任,而且造成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至今仍然無法突破對鄧小平一九八零年代改革開放的幻覺。」
一次反對中共,一生都反對中共
一九九七年,吳建民提前獲釋。南京國安不允許他在戶籍所在地南京工作和生活,他只好到無錫經商。
一九九零年代末以來,吳建民經商有成,創建的廣告公司擁有兩百多名員工,在當地排名前三甲,但他的公司無法到銀行貸款——他和他的公司早已上了黑名單。像他這樣的政治犯做生意,只能是小規模,只能「小富即安」,若是企業發展大了,就會被盯上並搞掉。他致富了,在社會上是有頭有臉的企業老總,是當地商會的秘書長。然而,「六四」的標籤一輩子都貼在他身上,他剛開始談戀愛,女友的家人就受到國安恐嚇。他與第一任女友到了談婚論嫁階段,女友的父親是一名高工,強迫他寫一份絕不參加政治活動的保證書,他拒絕此一無理要求,這樁婚事就告吹了。
中國政府用有限的賺錢的自由來鎖定民眾,導致「六四」後沒有幾年,民風驟變,唯利是圖。中產階級群體中,並未如西方現代化理論那樣出現民主訴求,政治冷漠症非常普遍。美國政治學家薩托利在《民主新論》中指出,在很多國家,公民的冷漠症和非政治化是普遍的,且跟貧困和教育水平低下無關。「即使人人都受過大學教育,也沒有理由期待人口中的政治覺悟會有顯著的變化。普通教育不太可能帶來政治教育得到明顯改善的公眾。」經濟學家熊彼得也說:「典型的公民只要一進入政治領域,其思維能力就會降至更低的水平,他將在他的現實利益範圍以內,以隨時準備承認自己的幼稚的方式去進行評論和分析。他再次成了原始人。他的思想變得易於人云亦云,易於受到感染。」
雖然有錢了,吳建民仍然缺乏安全感和尊嚴感。他的護照被國安扣在手上,他要出國洽談商務,國安派人與之同行。後來,他組織小區業主維權,對抗大型國企蘇豪集團和華潤集團。這場維權活動並不涉及政治訴求,只是捍衛業主的經濟利益,最後大獲全勝。但在此過程中,他傑出的組織管理才能再度引起中共當局的警惕。若是每一個像吳建民這樣的業主委員會主任都轉變成基層政治運動的號召者,中共的權力必然受到挑戰。這也是後來中共出重手打壓業主維權運動的根本原因。
吳建民對「六四」念念不忘,總是想着繼續做點事情。習近平剛上台時,中國國內出現一股樂觀氣氛,他和友人覺得可以通過舉辦大型的紀念趙紫陽的活動來為「六四」正名打開一個突破口。然而,二零一四年,廣州原高自聯領袖於世文和妻子陳衛因在黃河大堤上公祭趙紫陽而被捕。由此,吳建民得出結論:習近平與毛澤東和鄧小平一樣是獨裁者,是民主的敵人,正如薩利托所論:「民主就是非個人獨裁,是個人獨裁的準確的對比詞和確定無疑的對立詞。這意味着民主是指以反對個人化的權力、反對統治公民的權力屬於某個人為特徵的一種政治制度。權力不是任何人的『財產』。更具體地說,民主制度信守的原則是:誰也不能自封為統治者、誰也不能以個人名義不可改變地掌握權力。正是由於否定了個人獨裁的原則,民主準則才成為人對人的權力只能由他人授予,並且它總是且只能是在可以改變的基礎上。因此,領導者必須是從被領導者自由的、不受約束的選舉中產生。」百年來,中國的反民主本質從未改變過,追求民主就必須反共。
二零一四年,吳建民的一位在中央機關工作發小給他發來警示:在一份重要的黑名單上出現了他的名字。後來,這張名單上的人大都在「七零九」大抓捕中落網。在「七零九」前數月,吳建民攜妻子和雙胞胎兒女流亡美國,可謂間不容髮。在美國這個自由之地,他創建名為「建民推牆」的自媒體,「每天一講」,類似於當年冉雲飛的「每天一博」,已做了兩千多期節目,突破中共網路封鎖,吸引數十萬國內外受眾,幾乎以一人之力對抗新華社和央視的洗腦宣傳。從「六四」的廣場走向自媒體,反抗的方式「進化」了,但他對民主自由的信念,始終如一、痴心不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文由看新聞網轉載發布,僅代表原作者或原平台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立場。 看新聞網僅提供信息發布平台,文章或有適當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