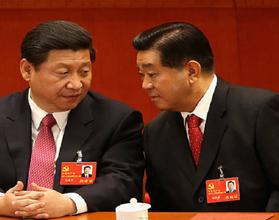國字頭的一般都是好東西,如國魂、國士、國學。但也有些壞的,為了強調其壞的危害程度,前面加個「國」字,如國賊、國恥和國足。
國賊可以清除,國恥可以洗雪,可拿國足怎麼辦呢?
國家太把足球當個事了,給編制,包費用,管足球的領導一大堆,幾乎每個球員都有頂戴花翎的機會。豢養足球幾十年,雖然沒培養出一支好球隊,但卻培養了一大批處級以上「優秀」幹部和富翁。足球訓練基地,更像是富翁和幹部栽培基地。國足就是寄生在國家肌體上囊腫,捨不得割,又痒痒,得時時撓。撓了幾十年,到了切割的時候了。
國足在虎年的大年初一,不負眾望地輸給了越南,會不會讓國家痛下決心,放棄國足?民諺曰:毒蛇在握,壯士斷腕。國足倒沒有毒性,但四腳蛇在握,也膈應人不是?必須斷腕。
國足到了「小崗村」時刻了——權力部門不管你們了,自己謀生路去吧!
權力曾經躊躇滿志,不相信搞不好農業,可費心巴力三十年,農民愣是填不飽肚子。被迫放權,讓農民自救。權力若拋棄了足球,沒準會帶來足球的崛起。
權力是以傲慢、任性及自信為特徵的,它不相信能有辦不到的事,只要集中力量就能辦大事。但一個小小的足球就憋紫了權力的大臉盤子,這麼個圓乎乎的小東西愣是玩不轉。足球就是讓權力一次次跌倒的「滑鐵擼」,一隻皮球仿佛成了鐵球,又硬又滑擼不起來,一不留神還砸了自己的腳。
中國足球為什麼擼起不來?因為權力太喜歡她了,受不起權力的纏綿寵幸及霸王硬上弓。權力急得團團轉:哄着上不了,硬着上不去,咋能把它摁住呢?
可以馴化老虎鑽火圈,馴化猴子騎車,馴化人跳忠字舞,卻馴化不了足球。體育取得的成就基本靠摹仿馬戲團的馴化方式。前體育領導發誓說:三大球不翻身,死不瞑目!三大球真的沒能讓元帥合上眼就走了。權力馴化足球如同用籠子圈養自由,是個竹籃打水的經典案例。
以前學界時常探討權力的邊界,公權和私權的界限劃分問題,「群己權界論」。說到動情時,就引用「紅磨坊」的故事,闡明私權對王權說「不」的地方就是權力的邊界。一首洋歌謠「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如天籟之音,讓我們聽慣了「盼闖王,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的耳朵很茫然:闖王要來也不讓進?他就闖誰攔得住!在我們這圪垯,得了權或丟了權就是權力的邊界。
晉惠帝是歷史上對權力有邊界意識的唯一領導。有一次他聽到青蛙叫,就發問:是官家的蛙還是私家的蛙?這真是千古一問!應該看作是「群己權界論」的先聲。可惜如此超前的好領導一直被抹黑成白痴了。我們的權力觀是沒有邊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蛙。
順便說一句,晉惠帝還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胸懷,那句被當作笑話的「何不食肉糜」,就體現了對平等主義的追求。多少志士,不就是抱着讓普天下人民都喝上肉湯的理想走上革命道路的嗎?雖然革命成功後,只顧自己吃肉,忘了給百姓喝肉糜,那也是狼多肉少造成的嘛。
權力可以強行讓人少生育,卻無法命令豬多生育;可以強拆豬圈,卻無法控制豬肉的價格。偉大領袖曾發出「大養其豬」的最高指示,也沒讓人民吃上肉,城市的肉票是硬通貨,有錢無票也買不到豬肉。權力能推翻「三座大山」,卻不能讓人民吃上肉糜,「何不食肉糜」劃出權力無能的底線。
權力興奮時,能砍光全國的大樹煉鋼鐵,能讓城市看不到一個乞丐,卻練不出真鋼來,也不能讓畝產真的達到十萬斤,更無法讓人吃飽飯。人民公社大食堂,就是把晉惠帝「何不食肉糜」的遺志化為現實的「偉大」實踐。
在權力不狂放時,殫精竭慮也解決不了農民的吃飯問題。直到權力「棄權」了,不管了,讓小崗村們自己討生活、逃活路時,糧食就在權力的縫隙里年年豐收了。
權力放過什麼,什麼就生機勃勃。重視什麼,什麼就奄奄一息。當年權力最重視文藝,江旗手親自抓文藝,跟後來的大抓足球有一拼。結果全國就剩下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北朝鮮的爛電影讓舉國若狂,國人仿佛在搶精神救濟糧。
權力只適合當特權消費者,不能當生產者。喜歡什麼,只要價錢合適,自會有生產者供應。就像宋徽宗喜歡天然野生美女,就花錢出宮去約李師師,不會招進宮來管理起來,也不派太尉級幹部當青協主席,經營青樓。老佛爺喜歡京劇,就出錢請進宮裡唱堂會,而不會給楊小樓戲班子編制,讓李蓮英管理成國營京劇團。據說想吃糖葫蘆也是叫外賣,沒在御膳房成立糖葫蘆協作辦。喜歡足球,也不用專門的局級班子管理足球,決定教練和球員人選、訓練方法及陣型戰術。
過去官企搞不好,就是因為權力根本不是財富的生產者,只能是消費者。權力要放棄生產,留出空間,需求什麼自然會有優質供應者,包括文藝、足球。權力只需要提供法治秩序,收取租賃費就very ok了。
韋小寶身居高位,一心想辭官辦麗夏院、麗秋院、麗冬院,也不是為了自己打茶圍方便,而是扎紮實實的經營。韋爵爺都明白,為了自己消費方便就自當老鴇子肯定經營不好,自給自足是權力的死穴。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一丘萬壑)
本文由看新聞網轉載發布,僅代表原作者或原平台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立場。 看新聞網僅提供信息發布平台,文章或有適當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