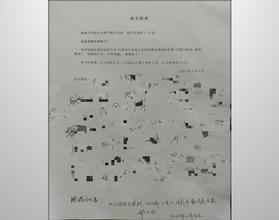在國內,爛尾樓是房地產在城郊腫瘤化擴張的產物,而住進爛尾樓,是抗爭的最後手段。
本文首發於NOWNESS,編輯當時找到我,想讓我採訪拍攝爛尾樓的攝影師。聊了幾句,我發現攝影師就是拍了幾張照片,根本不了解他們的具體生活。底層的苦難又被輕易地被利用,成為創作者的文化資本。在一家以圖片為主的文化媒體,我能做的,是用文字儘可能還原爛尾樓里的生活,但單獨的描寫和拍照一樣,是輕飄飄的。因此,我在文末做了一些資料上的總結。在國內,爛尾樓是房地產在城郊腫瘤化擴張的產物,而住進爛尾樓,是抗爭的最後手段。
2022年四月,攝影師Thomas看到了up主@環華十年 拍攝的爛尾樓系列。位於西安灞橋區的「易合坊」,爛尾七年,今年三月開始,陸續有三百多戶住戶搬進了爛尾樓。
這個本應在2015年交房的小區,外面堆着建築垃圾,建築只有一個主體的灰色框架結構,還沒封窗戶。電梯不通,也沒通水電。業主們把簡易的床板拉進爛尾樓里,有些就直接搭了帳篷、打了地鋪。夜晚,靠着一點太陽能板積蓄的能量,發出一團慘白的燈光。
一個67歲的奶奶住在十三層。前幾年出了事故,花了很大力氣才保住腿,腰上打了十幾個螺絲,背上還有二十幾個螺絲。她每天提着水桶上下十三層,一趟就要半個小時。而這個房子,本來是用來養老的。
住在爛尾樓里的人,每一戶都有自己的不幸:掏空了兩代人的積蓄,既要還貸,又要付房租;本來是婚房,現在孩子都上小學了;本來是婚房,因為爛尾樓已經離婚了。
Thomas發現這樣住進爛尾樓里的人,並不是個例。平常他是風光攝影師,坐着火車游中國。現在,他覺得有必要記錄時代變遷下人的境況。六月,他從重慶出發,先後去了西安、鄭州、青島的幾個爛尾樓盤。
慘敗的光
攝影師Thomas第一次真正走進西安「錦嶺公寓」的時候,像踏入一片廢墟。只有晚上亮起燈光時,才會注意到裡面住了人。和遠處的萬家燈火相比,爛尾樓里的光慘敗、小團,聚不成氣候。
晚飯時間,十幾個業主圍在一起吃飯。他們在一樓搭了一個臨時的公共食堂,輪流做飯。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個男人在木板搭出的簡易灶台上掌勺,兩個人在旁邊拿着手電,給他打光。他炒了一大鍋青菜炒麵,一人分走一碗。
王立是今年五月份搬進「錦嶺公寓」的,帶着兩個孩子,一個五歲,一個兩歲。對別人來說,這是西安高新區的一幢爛尾樓。對他來說,這是「家」。與他一同搬進爛尾樓的,還有100多戶業主,接近總數的三分之一。
沿着一段沒有整修的土路,一幢高樓突兀地立在一片荒地上。外圍的施工設施都沒拆,雜草的高度已經蓋過了建築垃圾。「錦嶺公寓」於2015年開工,本應在2017年10月交房。三棟樓,一棟爛尾,還有兩棟根本沒動工。
王立的房子位於八樓,他買來最便宜的地板革,往上一鋪,把床板和家具抬上去。找了一塊矮木板擋住窗戶,防止孩子頑皮掉下去。入住後,開發商切斷了他們的水電,把臨時廁所鎖住。業主們只好在旁邊挖了個旱廁。喝水是最大的問題,他們得把純淨水從一樓提上去。
孩子對爛尾房沒有太多概念,有時會問,「我們的家怎麼這麼髒?」,而王立小兩口已經在儘量維持家的整潔了。
「錦嶺公寓」位於西安高新區,距離市中心有二十幾公里。2010年前後,城市向外擴張,本是郊區的高新區成為眾多開發商搶地的地盤,一座座高層小區拔地而起,拓展了城市的高度和圍度。王立在2017年買下「錦嶺公寓」的一套三室一廳的戶型,九十平。全款四十多萬,掏空了父母和小倆口的積蓄。那時候結婚兩年,孩子剛出生,他想給孩子一個家。
「錦嶺公寓」的開發商是西安華岳實業有限公司,是西安本地的小開發商。買的時候,王立特地注意了樓盤的證件,確保「五證齊全」才敢簽訂合同。誰知到了10月,本應交房的樓盤卻停工了。
2018年,開發商說要復工,讓業主補齊尾款進行自救。兩百多戶業主東拼西湊九百多萬交給開發商,有些人還是借的信用卡甚至高利貸。他們滿懷希望地看到幾個工人在工地幹了十幾天活,之後又沒了動靜。
今年西安疫情,整座城市靜默。對從事零工、服務行業的人來說,「手停口停」。王立平常跑貨拉拉,封控的幾個月,他沒有拿到通行證。再出來幹活,經濟蕭條,一天都掙不了幾個錢。作為家裡唯一個賺錢的人,上有老下有小,一千多的房租無以為繼。
「要不是沒有辦法了,誰會住進爛尾樓?」疫情的衝擊下,大多數業主的生活都入不敷出。做小生意的無法開門,打工的沒有活干。對很多業主來說,這幢房子是他們全部的資產,掏空了全部積蓄,還欠了一屁股債。
這幾年,業主和開發商打過官司,打贏了,沒法強制執行。王立也一直在維權的路上,開發商和政府兩頭跑,沒有下文。住進爛尾樓或許是他們最後的抗爭手段。
西安的夏天酷暑難挨,40度以上是常事。對住在爛尾樓里的人來說,一切的不方便,都只能硬抗。王立說,自己從農村出來,吃點苦沒什麼,睡大街、打地鋪、住帳篷都可以。令人心疼的是孩子,夏天的蚊子毒,「孩子全身都起了疙瘩。」
眼看着孩子都要上小學了,爛尾樓落不了戶,孩子的教育成了問題。這幾年,王立帶着孩子,在西安的城郊之間輾轉。城市發展越來越快,城中村陸續被拆遷,便宜的房子越來越少。而因為這棟爛尾樓,王立申請不了公租房。
爛尾的五年間,旁邊的小區已經陸續建好,發展出配套的生活區、商業區。唯獨這幢高樓被落在後面,閃着幽暗的白光,顯得荒誕又詭異。
公社生活
Thomas是在抖音上找到@即墨香香哥 的,這個三十幾歲的年輕人,戴着眼鏡,斯斯文文的。從2021年10月開始,香香哥做了180場直播,記錄他的爛尾樓生活。
房子的二樓,臨時性地砌了幾排磚。搬進爛尾樓的業主,在「陽台」上放了一盆綠植。
這個爛尾樓盤,叫「香榭麗舍」,位於青島市即墨區的市中心。兩幢高層共有289戶人家。站在下面仰看,只有灰色的基本框架,連門窗都沒有。
香香哥的房子在13樓。他是農村長大的孩子,從小夢想有一天能住進高層。站在這間複式,相當於普通樓房26層的高度,他可以看到半個即墨區的夜景。只不過,爬上這13層,中途不休息,需要20分鐘。
買房是順其自然的事情。2014年,香香哥的孩子剛出生,想儘快從父母家搬出來。回想起來,那時候開發商的資金鍊已經出了問題。全款50多萬的房子,香香哥先是交了20多萬的首付,開發商以各種理由搪塞貸款的進度,最後以降價為誘惑勸說香香哥一次性交全款。首付已經掏空了兩代人的錢包,香香哥又管朋友借了錢才交上房款。
那時,在他的眼裡,根本沒有「爛尾樓」這個概念。何況這是當時的熱門樓盤,地段好,要托熟人關係才能買上。
買完房不出幾個月,工地上的人越來越少,最後在2014年末徹底停工,至今已經爛尾九個年頭。這九年裡,大部分業主一邊租着房、一邊還着房貸。房貸都快還完了,房子還沒完工。而香香哥也有了第二個孩子,一家六口人,擠在父母70平的房子裡。
2017年,即墨市「撤市劃區」,變成即墨區,房價暴漲。相比2014年,現在的房價已經翻倍了。當時香香哥的房子,買一層送一層,相當於有110平。按現在的市價計算,得要150多萬。香香哥已經買不起另一套房了。
2021年6月開始,幾位業主陸續在二樓搭起了一個據點,放了帳篷、桌子。香香哥有了一件專屬的「業主委員會」,他們想憑自己的力量,把房子裝起來。幾個業主算了一筆帳,每年房租兩萬,如果拿出來簡單裝修,就可以住進自己的房子。之後條件好了,再改善公共區域、比如水電、扶手,甚至布置院子。
在其他業主看來,住進爛尾路像是住進虛幻的海市蜃樓。香香哥他們幾個,想給其他人打個樣。
他們把房子樓下堆的建築垃圾用挖掘機清理走,弄了一塊公共區域。有時候,他們就在這裡做大鍋飯,用的是農村的大鐵鍋,撿拾一些建築廢料當柴火。
青島多雨,由於沒有封閉,挖的地下二樓已經變成一個「蓄水池」。整幢樓的基底,就這麼一直泡在水裡。六月的一場暴風雨,吹倒了臨時的鐵皮圍欄、也把他們辛苦收拾的院子吹得七零八落。
沒有門窗,幾個業主從二手市場淘回了防盜門,接力背着上樓。香香哥給自己家裝上門窗的那刻,他覺得有家了,「只不過是自己準備的鑰匙。」
這裡成了幾個業主臨時的據點。大部分時間,香香哥在做他的銷售工作,還是住在父母那裡。下班或者周末的時候,就去樓里整修自己的房子,偶爾幹活累了,會在二樓的帳篷里過夜,一點一點收拾出自己的屋子。
自從房子爛尾以來,香香哥一直密切關注全國爛尾樓的動態。在他看來,「爛尾樓」要得到解決,要麼寄希望於開發商,要麼由政府介入、進行兜底。兩種方法他們都嘗試了很久。現在只能「自救」,「我們業主自己變成了開發商,買的經濟適用房變成了自建房。」
周末的「香榭麗舍」格外熱鬧,幾位業主帶着自己的孩子,聊聊工作,孩子們一起玩耍。他們還一起在荒地上開闢了一塊菜地,種了菠菜、蔥、辣椒、西紅柿、韭菜,在菜地里拔一些自己種的蔬菜,用土灶做一頓「大鍋飯」,過成了「公社生活」。
何時搬出爛尾樓?
從西安到鄭州的火車將近7個小時。當火車快到達鄭州站時,Thomas看到鄭州之行的目的地,「豫森城」,就矗立在鐵軌旁邊。高樓上密密麻麻的空洞觸目驚心,「陰森,看上去死氣沉沉的。」每個空洞後面,都是一個遭受重創的家庭。
在Thomas兩周多的爛尾樓之旅中,鄭州的「豫森城」是一個奇怪的存在。在《南方人物周刊》的報道里,2020年,十幾戶人家住進「爛尾樓」,45天後潦草收場。「豫森城」的地塊,原來是大孟砦村,現在,村民們已經在爛尾樓底下的臨時安置房裡住了七八年。
這是一排由鐵皮組合而成的棚戶房。村民抗拒Thomas的鏡頭,拒絕了他想進屋拍攝的請求。他只能遠遠按下幾張快門。
河南是全國爛尾樓最多的省份,南陽被稱為「爛尾樓之都」。《南方周末》的報道顯示,2019年,南陽有302個爛尾樓盤。2012年,南陽開啟大規模城市建設,五萬多人因此搬遷,大大小小的開發商湧入南陽,地方政府默許開發商在五證不全的情況下蓋房甚至出售。
南陽是近十年中國城市激進擴張的一個縮影。在老城的外圍,開發商搶占地盤,一座座高樓在城市的新區拔地而起,許諾着現代化的美好生活願景。過去10年間,中國約80%的新房都是預售,預售所得成為開發商的最大資金來源,他們依靠增加未完工樓盤的銷售來維持資金流動。監管不力的情況下,一旦資金鍊斷裂,房子就有了爛尾的風險。
2020年,昆明的爛尾7年的樓盤,「別樣幸福城」,幾百戶業主住進爛尾樓。這是媒體對住進爛尾樓第一次的大規模報道。「住進爛尾樓」成為業主們自救的最後方式。
今年6月,河南鄭州的幾個樓盤相繼發布「停貸通知書」。據開源平台 GitHub 數據,鄭州有45個樓盤宣布「斷供」。這是自斷手腳的抗爭方式。業主可能會成為和開發商一樣的「老賴」,徵信出現問題。
對「錦嶺公寓」和「香榭麗舍」的業主來說,全款買的房,甚至都無法「斷供」。這種方法只對剛爛尾的樓盤奏效。銀行和開發商,還在乎後續那一筆錢。
在Thomas看來,「住進爛尾樓」是一個暫時性的現象。隨着關注度的上升,業主們或被驅趕、或被安置、或等到了樓盤復工,都有可能。
在「錦嶺公寓」住了三個月後,八月,王立等來了復工的消息,一百多戶業主高高興興從爛尾樓搬了出來。但直至現在,工地上,仍遲遲未見工人的身影。
文章來源:Matters
本文由看新聞網轉載發布,僅代表原作者或原平台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立場。 看新聞網僅提供信息發布平台,文章或有適當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