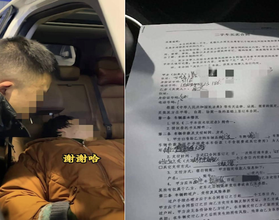昨天關於「何偉賣車」的文章沒了,這是意料之中的事。
有必要給大家匯報一下,已經有一些人聯繫了幫何偉賣車的朋友,大概率能夠成交,非常感謝大家。
其實我也有一個私心:如果實在沒人買我就買下來,作為有杏書店的一個「流動書攤」,上面放何偉的書,可以開到一些地方。
我自己買過所有何偉著作的英文版,全部都是在淘寶上買的,前些年淘寶店鋪還可以買英文原版書。
在他的所有書中,我最喜歡《甲骨文》。這本書中寫到陳夢家的故事,他在《1984》出版不久就讀了該書的英文版,文革開始不久,他看到一些場景,認為某種生活要來了,就選擇了自殺。
我碩士讀的是現代文學,早就知道作為詩人的陳夢家,他1949之後的經歷卻是我忽略的。也是在《甲骨文》中,我讀到了巫寧坤和他的《一滴淚》的故事,後來到處找《一滴淚》這本書。
這說明,何偉是懂中國的。
疫情開始,他在《紐約客》上的文章稱讚了防疫管控,這讓很多朋友感到不爽。我當時也很失望,後來能夠理解了:他是在為美國讀者寫作,心中作為對照的,可能是美國的「亂象」吧。
何偉是愛中國的。這種愛現在看來有點不合時宜,美國人怪他,一些中國人也怪他。
他的《尋路中國》在中國最受歡迎,可能是書名的原因。很多中國人也都在「尋路」,過去一百多年,大家都在尋找方向,這也是中國人熱愛宏大敘事的原因。
但是何偉對宏大敘事沒有太大興趣。我讀研究生時的一位同學,是何偉在涪陵師專當外教時候的同事。她昨天轉發我的文章,告訴我:在涪陵的時候,何偉和「同事們」其實沒怎麼成為朋友,大家因為種種原因,對這個外國人有所警惕。
和他成為朋友的,是他的學生和他接觸的「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人,後來他一直關心自己當初的學生,就像一個普通而熱忱的老師一樣。這是理解何偉最重要的一個角度:他關心的是中國普通人,而他也把自己當成是普通人。
或許正因為如此,他才在中國擁有這麼多讀者。他對中國的理解,是「正確的」嗎?或者是「深刻的」嗎?這並不重要,因為中國是如此複雜,並不是只有一個簡單的答案。
但是,有一點是真實的:他對中國的理解,擁有廣泛的共鳴。
他的意義也在這裡:給中人一個視角,「原來我們在一個美國人眼中是這樣的。」很多人因為這個視角,獲得了某種靈魂出竅的時刻,有溫暖有鼓勵,也有珍貴的幽默感。
對讀者來說,這是最好的時刻。就像周有光先生有一次強調的,「要從世界看中國,而不是從中國看世界」。但是,作為中國人,出國很難,外語又不好,你如何能夠從世界看中國呢?何偉就是老天給大家的那雙慧眼。
這種「外部視角」當然也有局限。但是我仍然認為這很珍貴,而且心存感激。
最近在讀哈佛大學教授裴宜理的一些書。她1948年出生在上海,父親是當時聖約翰大學(周有光就是從這裡畢業)的老師。1950年,裴宜理和父母一起到東京,等讀大學才回到美國。她在一本書的前言中談到,自己對中國的感情,使用了「回到故鄉」這樣的說法。
她對「中國革命」的一些看法,一些人也不認可。但是,她博士研究的是「華北革命」,中國剛開放國門,她就申請到南京大學訪學,到「淮北地區」實地調查,這真的很可貴。
我願意把這理解為「人類身上珍貴的天真」。
我在哥大訪學,有一次拜訪黎教授,他已經很多年不能到中國了,但是一直在幫助到紐約的中國人,幫高耀潔解決在紐約的各種生活難題(剛來的時候甚至陪她買麵包),申請低保,組織一個學生小組,這麼多年一直堅持幫助高醫生。
我問他一個很「中國式」的問題:你幫助過這麼多中國人,誰最讓你失望?
我想,一定有忘恩負義、或者後來變得不太體面的人。他笑了:沒有,沒有一個人讓我失望。這就是「珍貴的天真」。如果有這種「分別心」和功利心,他就不可能堅持這麼多年,對中國人「無差別」的愛。
我認為何偉身上也有這種天真。如果沒有這樣的天真,一個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生,為什麼要跑到中國去呢。
有一次見到Ian Johnson,他知道我從成都來的,告訴我:「我和Peter是好朋友。」「哪個Peter?啊,是何偉,Peter Hessler。」
車賣掉,可能,他以後就變回Peter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
本文由看新聞網轉載發布,僅代表原作者或原平台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立場。 看新聞網僅提供信息發布平台,文章或有適當刪改。